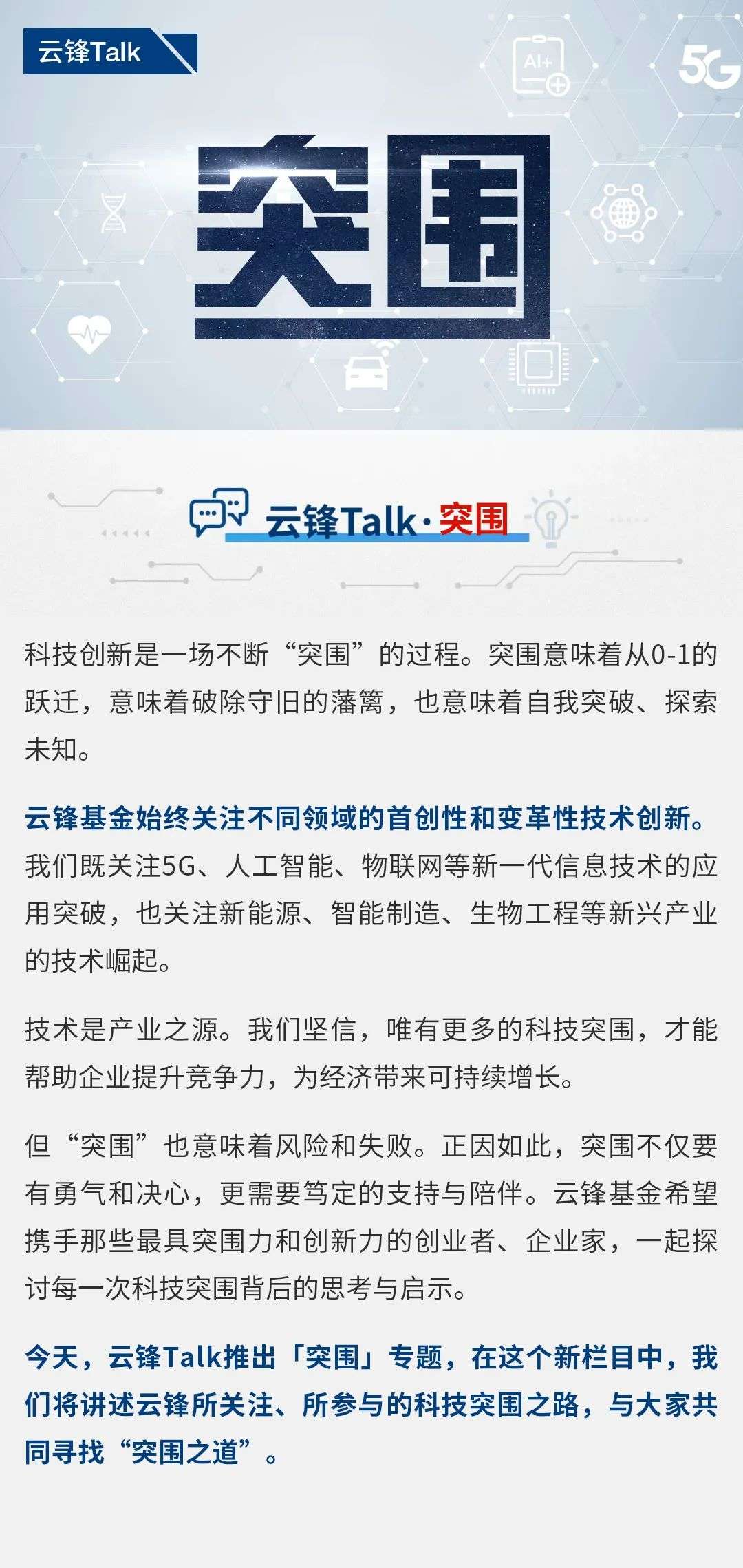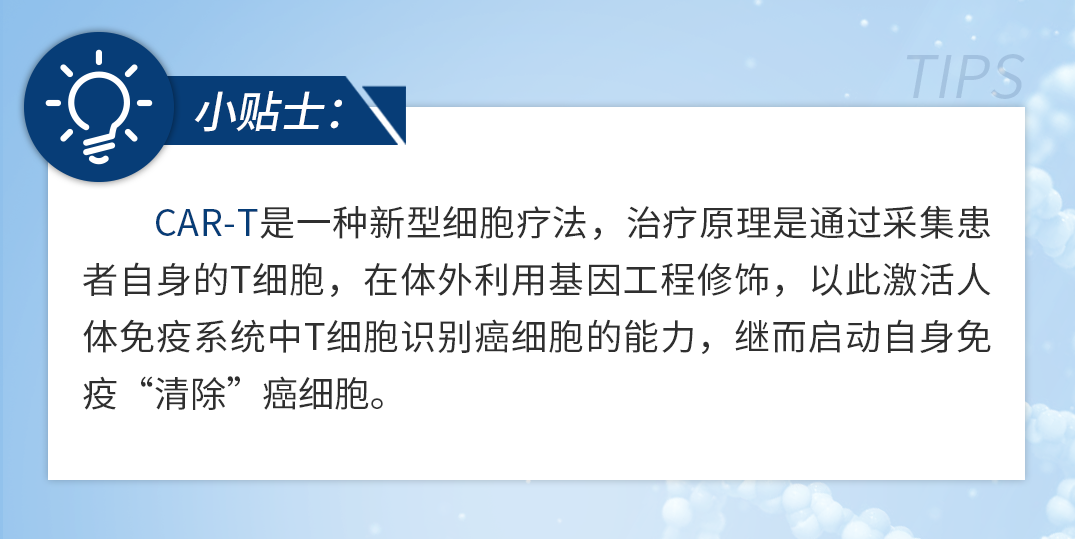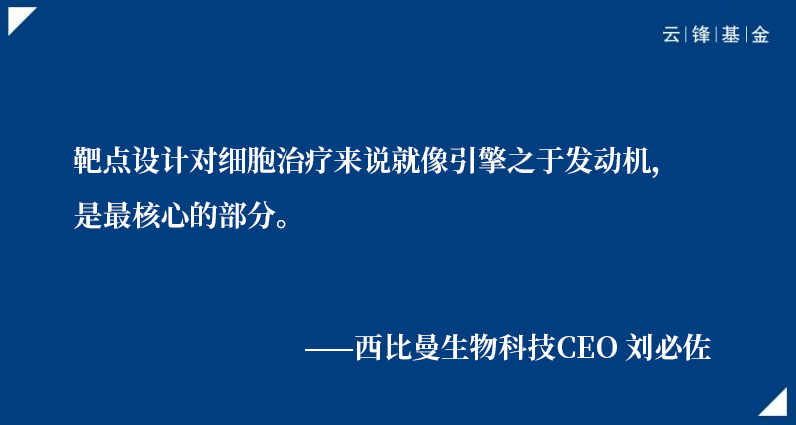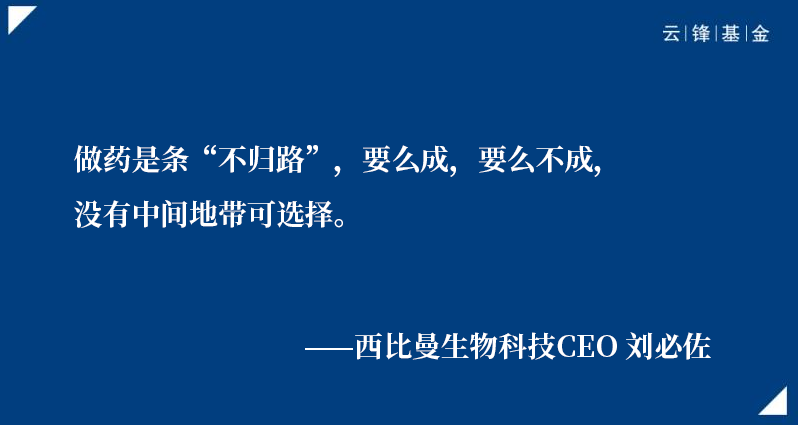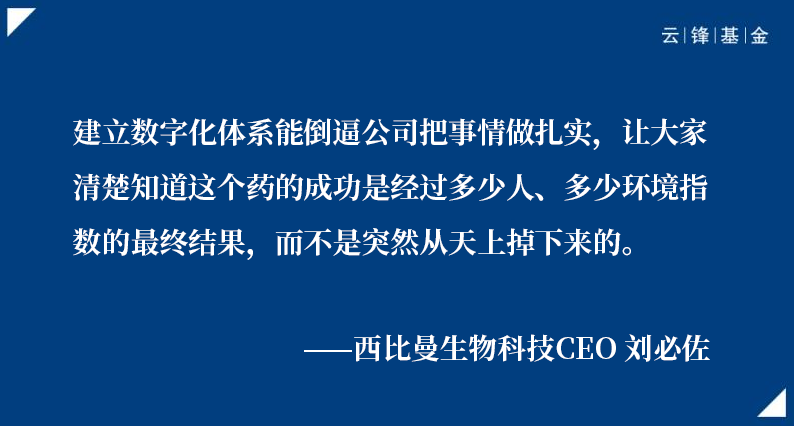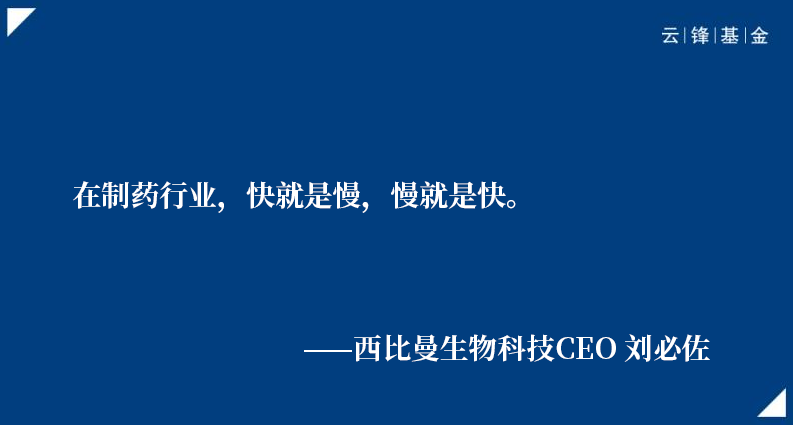西比曼刘必佐:只有敢于做突破性选择,才能拿到突破性结果|云锋Talk·突围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云锋基金”,36氪经授权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制药业始终保持着模仿和跟随的后进姿态。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中国正在从仿制药大国转变为创新药大国,尤其是在细胞治疗领域。”西比曼生物科技CEO刘必佐说。西比曼生物(CBMG)是国内细胞治疗领域的先行者,早在2015年便率先启动细胞治疗淋巴癌的临床项目。
细胞治疗着眼于“治愈”癌症,被誉为是目前最有希望攻克癌症的疗法。CAR-T作为一种新型细胞疗法,其在血液肿瘤的治疗中已经表现出显著疗效。
不同于传统药物,CAR-T疗法是一种个体化定制药品,每个产品都源于患者自身的T细胞,不仅开发和生产过程复杂,在制造和交付上也有极高的精准度要求。这意味着,生产工艺的“稳定性”对细胞治疗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为此,西比曼在过去六年完成三件大事:建立一流研发创新团队,精进生产工艺并搭建数字化体系,加速临床验证。在刘必佐看来,专业人才、生产工艺、数字化能力将是公司未来稳步前行之根本。
刘必佐是互联网老兵,加入西比曼前,曾在微软和阿里巴巴任职二十余年。过去的从业经历让刘必佐更能跳出行业视角,思考如何用数字化方式为生物科技注入新的动能。刘必佐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带领西比曼成为leader,而不是follower。
今年6月,西比曼双靶点CAR-T产品获得FDA孤儿药资格认定,这是国内首款靶向CD19/CD20的细胞治疗药物,高达92.6%的总缓解率更让滤泡性淋巴瘤患者看到被治愈的曙光。
云锋基金一直支持技术创新,关注投资从事First-in-class/Best-in-class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今年2月,云锋基金等买方团完成对西比曼的私有化交易,助力公司为全球癌症患者带来高质量的创新型药物。
本期「云锋Talk·突围」,刘必佐分享了细胞治疗行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西比曼在靶点设计、生产工艺、数字化项目中所做出的突破性选择,以及从互联网跨界生物科技行业的心路历程。
以下为对话节选,enjoy:
谈挑战:靶点选择决定治疗潜力
在免疫细胞治疗尚未成为主流的2015年,西比曼就进入这一领域,当时做出这一业务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刘必佐: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偶然的,当时我有个朋友在做这类产品,他们对病人的免疫系统做一些研究,而且研究结果不错,我当时就判断免疫细胞治疗绝对是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因为西比曼此前一直做的是干细胞产品,属于再生医学,不在治疗疾病的范畴内,而癌症治疗绝对是未来的刚需。
第二是就我个人而言,在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中,有5位都得过癌症,我的父亲和两位舅舅都是因癌症去世的,所以自己有亲身体会,一旦家人得了癌症,亲人是很无助的,因为基本相当于被判了“死刑”。所以我下定决心,带领西比曼从干细胞拓宽到“干细胞+免疫细胞”领域。
CAR-T细胞疗法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在研发和治疗过程中通常会面临哪些挑战?
刘必佐:第一,研发新药,确定好靶点是重中之重。你是不是独特的,是否有特定IP,靶点设计对细胞治疗来说就像汽车里的引擎,是最核心的部分。第二,细胞治疗药物是活体药,打进人体后需要有效能,简单讲就是看细胞的“年轻程度”怎么样,只有保证细胞是“年轻”的,才能和癌症做斗争,这意味着生产工艺也是药物治疗的一部分,因此必须确保生产工艺的稳定性。
近期西比曼双靶点CAR-T产品获得FDA孤儿药资格认定,这款药物在靶点选择上面临哪些关键抉择?
刘必佐:第一是关于单、双靶点的选择。西比曼C-CAR039主要用于治疗滤泡性淋巴瘤,这个领域目前已有三家产品获批,分别是诺华、吉利德和药明巨诺的产品,但这三款药物都只靶向CD19。
我一直认为,做药应该追求最佳产品,要么是First-in-Class(同类第一),要么是Best-in-Class(同类最优),但现在First-in-Class已经做不到了,就得做到和别人有差异。因为CD19、CD20在B细胞肿瘤中都有特异性表达,我们就猜测CD19、CD20两个加在一起可能会效果更好,就去做了验证。
第二是关于具体靶点的选择。当时我们还有几款候选药物,行业中绝大多数双靶点CAR-T疗法都选择靶向CD19/CD22,甚至行业“医生大咖”所达成的共识也是认为CD19/CD22更好,原因是绝大部分病人在经过前面的标准治疗后,可能已经丢失了CD20。而且即便用CD20,也有不同设计的药物。
经过我们内部再三讨论,最终考虑到药物的专利性和新颖性,我们还是决定用一个strong IP,有特异性的CD19/CD20来作为最终的临床靶点。这个过程是最纠结的,因为当时CD19/CD20还没有完全被验证是可行的。
幸运的是,从现有临床数据来看,C-CAR039确实是Best-in-Class,对癌症的最佳缓解率能达到92.6%,显示出良好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靶点方向选择的正确与否,对药品研发意味着什么?
刘必佐:我们经常讲,做药就是“0或1”,要么成,要么不成,没有中间地带可选择。很有可能做了很多年,到最后是一场空,就因为一开始选错了方向。
我再打个比方,如果金矿在苏州,你却跑到杭州,那就是搞了个“乌龙”,而当你到杭州发现不对,再回去,就错过了时间窗口。所有企业都在找最好的药给病人,如果别人已经找到药,你才来,就只能变成Me-too/Me-better,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不同的市场挑战。所以在做药行业,大方向的选择非常重要。
你提到细胞治疗的生产环节也是一大挑战,西比曼选择了怎样的生产工艺?
刘必佐:因为GMP无尘车间不是简单的技术,每增加一天,人工成本、生产成本就会高很多。我们希望生产周期能最大程度缩短,还希望细胞越年轻越好,生产成本尽可能降低,所以我们在前人的生产工艺基础上,改善了第二代工艺,经过多次对比和尝试,最终采用封闭式系统,基本全部通过自动化、数字化来完成,大大缩减人力成本和生产周期。
在生物科技行业中,西比曼是少有对数字化生产投入很大的企业,这对药物的生产和治疗能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
刘必佐:我们从两年前开始在数字化上做投入,并且投入在千万元级别以上。因为细胞治疗药物的运输流程很长,从医院采集样本到生产基地制备,再回到医院回输,整个流程需要通过数字化对细胞治疗样本实现追踪,确保产品全程的可追溯性和规范性。第二是对治疗效果的帮助,我们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跟踪、收集和更新数据,慢慢就能对不同状态的病人做出精准评估,对药物做出相应调整,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除了对生产环节的追踪,数字化体系的建立对监管也有帮助。未来的监管趋势一定是实时的,像FDA在检查公司时,笔迹、时间不能有任何修改,甚至材料中撕掉一页纸也不行,这叫篡改数据。全部数字化以后,我们就有了block chain,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知道谁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这也是公司底气的象征。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倒逼大家把事情做扎实,让大家清楚知道这个药的成功是经过多少人、多少环境指数的最终结果,而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
谈竞争:雨后春笋与大浪淘沙共存
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推广,近两年CAR-T疗法所处的市场环境发生哪些变化?
刘必佐:第一是政策法规层面的变化。2017年底,国家食药监管局明确了细胞免疫治疗产品的药物属性,结束了多年来细胞免疫治疗是技术还是药品的争议。政策规范后,淘汰了一批公司,到今天,我认为第一梯队只有十家公司左右。
第二,能明显看到中国正在从仿制药大国转变为创新药大国,尤其是在细胞治疗领域。像西比曼生产的C-CAR039,是中国第一款靶向CD19/CD20的细胞治疗药物,不仅是西比曼,很多中国药企的产品也在从Me-too走向Best-in-Class,我相信在细胞治疗领域,不论产品还是生产工艺,中国未来都可能成为全球领导者。
为什么细胞治疗领域可能涌现更多的Best-in-Class产品,其中的驱动力是什么?
刘必佐:细胞治疗、基因治疗都讲究novelty,虽然大家做针对同一个靶点的药物,但每家的生产工艺、申报路径、疗效和副作用都不一样。
首先,相比大分子、小分子药物来说,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的研发周期更短,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在特定政策上给予了帮助。比如研究者发起一个细胞治疗研究,只要通过医院伦理审查,就可以在有资质的医院开展临床实验,从研发到临床的周期会大幅缩短。
第二,细胞治疗、基因治疗都是个性化治疗方式,跟数字化息息相关。现在人工智能在诊断、筛查、寻找靶点等环节都已经积累了大量数据,能加速新药的研发,也能一定程度上缩短研发周期。
哪怕像CBMG这样体量较小的公司,也有多款药物在同时研发,包括面向淋巴癌、白血病、肺癌、肝癌等。如果是过去所研发的小分子、大分子药物,我们这么小的公司不可能一下做这么多药。而我们这么做,其它公司也能这样做,我相信这么多药当中,肯定会有Best-in-Class/First-in-Class的出现。
有数据统计目前全球有超过600项CAR-T治疗的临床试验项目,你如何定义当下的市场竞争状态?
刘必佐:雨后春笋和大浪淘沙,这两种状态是共存的,而且我相信未来十年、二十年都会持续下去。
做药跟互联网不一样,互联网是“黑洞”,当数据越聚越多,壁垒就越来越高,后人难以入局。但做药是只要有novelty idea,雨后春笋就会一直出现,这是好事。而一旦大家知道哪几个靶点能够成药,就会出现严重的靶点扎堆现象,最后就看谁能最先把药做出来,并且做到最好,这时就会有大浪淘沙的情形出现。
即便前面已经有同类药品获批,后来者依然有进入的机会?
刘必佐:是的。以前确实是某款药先上市后就会把市场占领,其它药很难进来。但今天不一样,哪怕你后进来,但效果好、安全性好,别人也会选你,这也是为什么在医疗领域,临床数据的公开很重要,而且要全球公开,因为对病人来说,这是一次对生命的投票。
免疫治疗一直被冠以“天价药”的名头,在你看来,细胞疗法的商业化前景在哪里?
刘必佐:首先要确保它确实对癌症病人有帮助,在此基础上要解决谁买单的问题。我认为医保绝对是解决方案之一。
最近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关于CAR-T产品的价格,100多万看上去是高,那是因为企业此前连续投入了好几年的研发和生产成本,而且药品从前到后就是给这一位病人定制的,从采样本、生产制备、再打回体内,差不多有十几天时间,很多人力花在这里,这样算下来其实有一定合理性。
即便今天这个药不出现,一个癌症病人进入医院,也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治疗费用。相对来说,CAR-T疗法是更简单的治疗方式,而且它的副作用可以控制。
所以要解决支付问题,我认为初期方案可能是combination,自己拿一部分,医保拿一部分,当然如果医保能全部支付肯定更好,因为我国癌症病人每年新增400万人,它不是几百人、几千人,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病人这么多,早晚都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谈合作:强强联合是必然趋势
西比曼在过去5年一直实施研发中心、生产技术平台“两步走”的核心发展战略,你最终希望把西比曼做成一家怎样的企业?
刘必佐:我希望西比曼成为一家平台型公司,成为一个快速发展又具代表性的新型“大药厂”。想做到这点,我们必须依靠四个核心的building blocks:
第一是生产工艺。在行业中,我们一直以生产工艺为长,这里有很多trade secret、IP、know how,是我们的优势。第二是数字化,我们两年前开始在数字化领域做投入,我相信这会成为我们区别于其他生物制药公司的特质。第三,是QMS(质量管理体系)。做药的核心在于从研究到药的过程,我们2018年开始与诺华开展战略合作,相当于有一个“老大哥”在前面引路,教你怎么做药,所以不论是在研究阶段还是商业化阶段,西比曼这两年都有很大提升。第四,打造产品创新开发能力。这种产品开发可以通过内部,也可以通过外部合作方式完成,这样我们才会有源源不断的产品管线。另外,西比曼所有研发、生产的细胞产品必须通过GCP来进行临床验证,确保安全有效。
有了这四个building blocks作为底层驱动力,我们就可以通过不同形式来达到公司的最终目标。
在目前已经开展的合作中,西比曼分别扮演着哪些不同的角色?
刘必佐:在与诺华的合作中,他们授权西比曼在中国生产和供应诺华的CAR-T细胞疗法Kymriah,所以诺华看中的是我们的生产技术平台。在接近14个月的合作谈判中,我们通过了诺华的两次audit,这个检查目的在于对生产工艺的稳定性做评估。
我们还在与另一家大药厂开展有关实体瘤药物的研发合作。虽然细胞治疗在血液瘤治疗中展现出很好的疗效,但在实体瘤领域,即肺癌、肝癌、胃癌等方面面临的挑战还很大,所以我们希望以实体瘤作为突破口。
除此之外,我们跟GE、赛默飞、德国的Miltenyi也开展了深度战略合作。比如我们和GE一起开发了全球首个数字化半自动细胞生产系统,和赛默飞合作开发了西比曼特有的细胞培养耗材。
与这类顶级药企合作,给西比曼的研发和生产带来哪些促进作用?
刘必佐:以与诺华的合作为例,这直接帮助西比曼的生产工艺从研发阶段提升至商业化阶段。虽然细胞治疗药物是根据每位病人情况专门定制的,但在药品的物流运输温度控制、基本培养工艺等方面又具有一定共性。
制药的风险点在于,在细胞制备和运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潜在污染,这非常取决于生产工艺的稳定性,所以需要经过严格的1000多个规定性动作。西比曼现在生产方面有一整套完整的质控管理体系,有上千页的SOP,能保证第1个到第9999个病人的药都是合格有效的,这是像诺华这样的大药厂才可能教会你的。
在你看来,药企之间的强强联合是未来必然发展趋势吗?
刘必佐:一定是。细胞治疗不仅跟当地监管有关,跟受众人群也有关系,比如说诺华Kymriah这款药虽然已经在美国上市,但想要引进中国,还需要我们在生产和桥接试验上一起完成合作。
第二,从技术层面看,西比曼的优势在于我们打造了一个自动化、标准化、全程质控化的细胞生产平台,我们完全可以和大药厂合作,只要他们有好靶点,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平台上,共同生产开发,进行临床试验。从这个角度讲,西比曼更像一个“转化医学中心”。
第三,就资源来说,西比曼毕竟规模还小,如果让我们在海外成立一个大团队做生产、与药厂医院开展合作,那需要撬动的资源非常大,很不现实。所以自然而然地,合作就会出现。
合作只是过程,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强强联合,加快从研发到生产临床的速度,提高“治病救人”的效率。
谈管理:快就是慢,慢就是快
不论是进入CAR-T领域,搭建生产技术平台,还是推行数字化项目,你每次总能提前一步踏对方向的原因是什么?
刘必佐:这可能跟我的思考习惯有关,我通常会考虑五年以后会出现的情形,再为当下做决定。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CBMG想做一个百年老店该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想到搭建生产技术平台、数字化体系,这肯定是公司长期发展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就像2016年我们开始做CAR-T的时候,整个行业还是以“小作坊”为主,那时我们决定在张江拿一万平地建工厂,碰到很多阻力和质疑。但回过头看,如果没有这个工厂,也不会有诺华这个合作方。所以当你朝远看,想把公司做大,而不是光想着把今天这单做好,价值总有一天会凸显出来。
▲西比曼全球研发生产基地
你此前在互联网公司任职多年,互联网公司和生物制药公司在管理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刘必佐:管理生物制药公司的挑战很大,我说自己的时间30%花在协调人上一点不为过。我们公司有300多人,至少100多人都是MD、PhD、Postdoc,每个人都很牛,你怎么告诉他“你对,他对,她也对”,但是你们合作可能会更好,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做药的大部分结果都是失败的,所以药厂在做药时,更多时间是花在“去风险”上。最终到底做哪款产品,可能A、B、C每个人讲的都有道理,而作为CEO要听不同的声音,最后“搅和搅和”做出一个方向性决定,这个决定直接决定了药的成与不成,是非常艰难的。
第三,在这么多生物制药公司中,你必须找到自己的特色和差异。做药能否成功我们没法保证,但我要发挥生产工艺这个长板,相对而言我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点。
所以生物科技和互联网公司的管理确实不太一样,一方面是大的战略性挑战,另一方面做药是件非常细的事,那就意味着对细微、细小事情的处理要特别重视。
你通常如何做出这个艰难的方向性决定,每次决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刘必佐:这确实是个很核心的问题,互联网领域可能很快就能见到市场反映,GMV、活跃度一目了然。做药不一样,从研发、生产到临床,要等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能知道结果,所以往往做下这个决定后,压力会特别大。
坦白讲,这跟考试一样,首先要在前期做好充分准备,第二是及时并且经常和专家沟通,不行就重来。在这中间,只能等结果,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大部分做药的人头发都白了,做药是熬出来的。
西比曼是否形成了一套管理机制来降低这类风险?
刘必佐:一开始我们还是各部门分工明确,工艺部门只管生产,临床部门只管临床,互不干预。但经过实践,发现这种方法在细胞治疗领域不是最佳的管理方式,因为细胞治疗从前到后是个流水线,每个因素都可能改变药的最终结果,生产制备已经是贯穿整合制药流程的重要一环。
所以现在我们有个“会诊”机制,各部门VP级别以上高管组成委员会,大家每两周“会诊”一次,讨论核心项目的进展做法,有问题共同解决。在看临床结果时,我们还会叫上转化医学、生产工艺、质控等部门一起讨论,大家open debate,the best argument,best proven evidence,以此降低风险,一起做出改善和提升。
非常幸运,西比曼通过这种决定体系,在过去几年做对了几个重大决定:进入免疫细胞治疗领域;提早投入细胞生产自动化体系,扩大生产能力准备商业化;对研发团队进行投入,引进一批国际尖端人才;和国际顶级大药厂合作,等等。
作为跨界进入生物医药领域的CEO,你通常是如何自我迭代的?
刘必佐:我不是这个专业出身,可能看上去是个短板,但长处在于能够跳出行业视角,从局外想新方法。我曾和高管们讲,传统治疗方法如果不改进,就会落伍。就像数字化,如果用过去的传统方法,可能十年才能产生结果,但利用数字化以后,就能大幅缩短时间成本,降低成本和风险。
在自我迭代上,挑战确实很大,除了自我学习,我还经常请教外部专家,了解行业最新的变化趋势。我学习的目的肯定不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医学专家,但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对公司方向做出判断。
新药研发是个需要耐心的行业,但创业公司很强调成长速度,你如何理解创业过程的快与慢?
刘必佐:我经常和大家讲,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做药如果走得太快,把必须固有流程丢了,出现问题,后面就都是无用功,全得重头来过。所以必须把基本功做好,才能走得更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