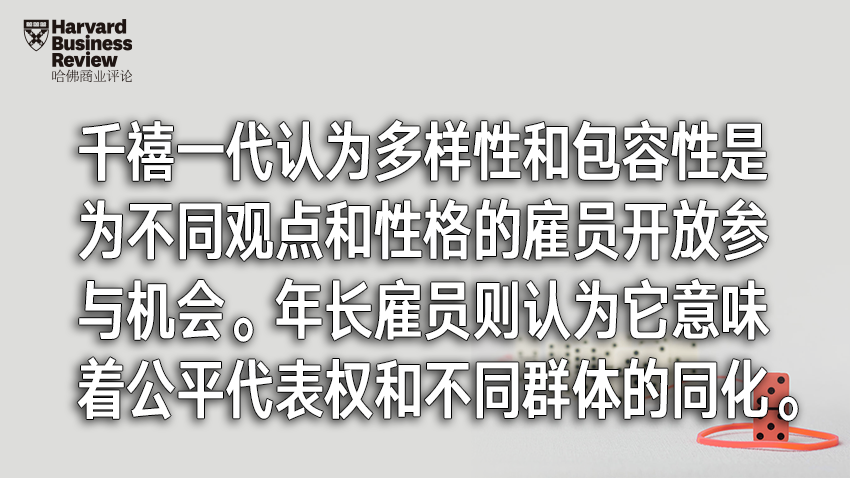努力和才华,为什么不一定能换来赏识?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哈佛商业评论”(ID:hbrchinese),作者:HBR-China,36氪经授权发布。
小佛爷说
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员工在多样性的工作环境中,有更高的决策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创新能力和灵活性。在如此丰富的证据面前,我们恐怕难以忽视多样性的益处。还有很多人认为,在企业做招聘、员工发展和薪资的相关决定时,应该按才能分配。尽管这两种看法并不矛盾,但在现实中却难以调和。因为认知问题常常会造成阻碍。
实力问题
在选才过程中,实力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筛选条件,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自认为能慧眼识才,而现实却恰恰相反——我们非常不擅长客观评价他人。正因为如此,管弦乐队几十年前就采用了盲选的方式;而今,程序和算法在选才方面也比人类更加智慧。许多公司仍在不断寻找能够取代传统绩效评估的新方法。
即使(特别是)领导者宣称自己会一碗水端平,却仍然会因为刻板印象,对表现相同的人予以差别对待。麻省理工学院的埃米利奥·卡斯蒂拉(Emilio Castilla)和印第安纳大学的斯蒂芬·贝纳德(Stephen Benard)在其著名的研究“精英制度的悖论”(paradox ofmeritocracy)中对此有过论证。
到底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成功和幸运》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H. Frank)提供了一种解释:我们未能看清偶发事件在生命轨迹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假如某人获得一份高薪且令人艳羡的工作,我们会将其视作个人努力和才华的结果(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而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呢?我们会告诉自己也许是他们不走运,但如果当初他们能再努力一点,还是有机会反败为胜的。
如果当权者认为这个世界是公平正义的,他们就会对体制的不公视而不见,更不会为此担忧。弗兰克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讨论不公的,但其意义对被忽视的群体来说不言自明。他深入钻研了大量社会学研究,发现运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成功,而我们极不情愿承认这点。
框架效应(指一个问题两种在逻辑意义上相似的说法却导致了不同的决策判断——译者注)或者直观的参考项(比如住在郊区或者在私立学校就读等)会影响我们对大千世界中贫富的观感。“后见之明”则影响我们的判断,让我们相信随机事件可以预测,并为自己成就的必然性作出一系列解释。而在胜者为王的世界中,“金字塔顶层的少数人手中掌握有多数财富”,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认知偏差,使我们得出不准确的结论。
我们当然更容易接受能力最终会受到赏识这种观点。正如弗兰克所说,如果我们认为通向成功的道路上有付出就有回报,不是碰运气,再对自己的能力略微高估,那么我们会更容易打起精神战胜困难。但是他也提出,这样的思维模式容易妨碍我们对整体经济增量有利的公众解决方案进行投资。
也许我们执着于此的最大原因是,每当这一观点被质疑时,我们都感同身受,仿佛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付诸东流。弗兰克表示,才华和努力的确非常重要,但它们往往无法确保成功。虽然改善公共政策和怀有感激之情有利于改善不公平的现象,但是我们离精英制度下的生活还很远,因为首先我们对于精英的看法就漏洞百出。
多样性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至少较为客观地)弄清在特定情境下才能的定义。假如才能真的可以定义,我们也能够抛弃偏见(这并不容易,因为偏见非常顽固),是不是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多样性?
很难说。因为定义本身就有争议。根据德勤的研究,千禧一代认为多样性和包容性是为不同观点和性格的雇员开放参与机会。年长雇员则相反,认为它意味着公平代表权和不同群体的同化。
即使选择第二种传统定义,我们又该如何制定目标并追踪进展呢?杜克大学的阿什雷·谢尔比·罗塞特(Ashleigh Shelby Rosette)在2016年沃顿人力分析大会上指出,人们喜欢用二分法分析事情——男性/女性,白人/黑人,多数/少数等。但是现实比这复杂得多。女性、黑人、穆斯林这些标签不能概括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内在相关联的不同属性的集合”,而在组织内部,很难准确分析和平衡这些属性。
还有一点也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修辞会影响我们理解权力的方式。罗塞塔和密歇根大学的同事莉·托斯特(Leigh Plunkett Tost)在心理学文章《理解社会不平等》中讨论了这一现象。总体来说,将不公平描述为某些群体的特权(而非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会让人们产生防备心理。这点和弗兰克所说的“天上掉馅饼”的好运类似,都损害了我们的自我形象——我拥有的难道不是自己努力才得到的吗?这样的认知会让我们刻意回避问题,而不想修正问题。
此外,身在不同群体的成员权力状态不同。一些人可能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地位很高,而在其他群体中很低。罗塞特和托斯特的研究表明,在某些群体里身为主导的人,如果在其他群体中体会过受别人支配的不公,就会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享受的特权(也能理解与自己相比没有优势的人)。例如,白人女性总体来说比男性更了解种族带给自己的优势,因为她们面临着性别歧视问题。
高层领导者须辨别出组织中的不公平,他们比普通人更需要这种能力,因为他们有能力带来改变。但是一旦得到高层职位,人们往往会忘记自己曾经遇到的障碍。罗塞特和托斯特发现,最终“他们缺乏动力和远见,不会去认真考虑主导群体享受的优势”。对于成功的白人空姐女性来说尤其如此。“比起白人男性来,她们更少提及白人享有的特权”。有趣的是,白人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并没有让她们在获得成功后理解自己享受的种族优势。也许是因为地位来之不易,她们下意识地谨慎行事,不想节外生枝。
除了定义不明确和具有防御性动机外,我们还要跨越更高级别的概念障碍:人类对多样性本身存在偏见。俄亥俄州立大学小罗伯特·劳特(Robert Lount Jr.)和同事(罗格斯大学的奥利弗·谢尔登Oliver Sheldon、格罗宁格大学的付罗尔·林克Floor Rink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凯瑟琳·菲利普Katherine Phillips)近期的研究表明,多数人认为多样性会带来人际冲突。
一组试验参与者分别朗读、阅读或听取了同样的几段对话,最后一致认为全部由黑人或白人组成的小组,比黑人和白人混搭的小组更加和谐。
如果我们认为人在多样性组织或团队中表现较差,那么我们会如何解读和奖励他们的实际表现呢?带着偏见?很有可能。
希望渺茫?
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认为,即使经过培训,试图战胜个人偏见的行为也是徒劳的。他认为,人类天生过度自信,所以会仓促得出结论,并做出下意识的判断。但是组织的思考和行动速度缓慢得多。组织有机会改进决策过程。
哈佛商学院的约翰·贝西尔斯(John Beshears)和弗兰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的研究支持这一看法。他们在《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写道,“重写人类大脑极为困难,”但是我们能够“改变决策的环境”。
这种方法(即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是缓解偏见,而非逆转偏见。贝西尔斯和吉诺的研究发现,这种方法在很多情况下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我们要慎重设计信息的表达方式和给出的选项:你不能剥夺个体做决定的权利,也不能告诉他们如何去做;而是要努力让他们更容易做出理性决定。
这里仍然有操控的因素:机构为某种类型的选择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会带我们回到共识(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多样性能够改进绩效,支持这一做法且表现优秀的员工应该得到公平对待。
如果组织成员识破了观念背后的事,是否会感到自己被迫做了不愿意的事情?也许吧——那又是另外一个需要清除的认知路障了。
关键词:人才管理
莉萨·伯勒尔|文
莉萨·伯勒尔是《哈佛商业评论》的高级编辑。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钮键军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