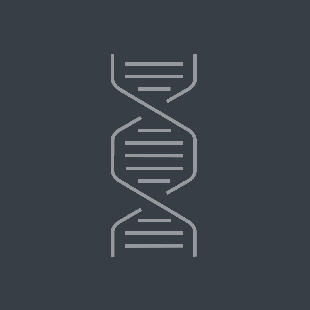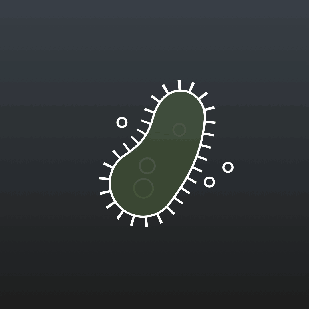A16Z合伙人:从药物发展史来看,“编程药物”将重构人类
编者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治疗疾病的药物也面临着转折,一些医药公司和科学家,正在考虑将人体细胞本身改造成药物的可能性。近日,A16Z的合伙人Jorge Conde发表一篇文章,详细梳理了药物的变迁史,以及新的变化将会如何发展,他认为,随着我们日益走向编程药物的社会,基因、细胞、微生物等药物将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反过来也将重新建构我们。
治疗师是一个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的职业。科学家目前发现,在公元前6500年前人类骨骼上就带有医疗干预的伤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还有在脑部做的手术。
但正式的医学实践历史要短得多。
在20世纪初,大多数医学院甚至不需要大学的教育水平;任何能够负担得起学费的申请人都能够被录取。
在很大程度上,医生被认为是和木工、铁匠一样的行业,有抱负的外科医生会在理发店当学徒,甚至许多哈佛医学院这样学校的学生都是半文盲。
直到上个世纪,美国的医学教育才变得专业化,成为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的科学和正规实践。
当然,在同一时期,我们也看到了医学上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尤其是在公共卫生领域,通过在全球疫苗接种上的努力,许多疾病几乎被根除了。
新兴的诊断平台和生物标志物(如胆固醇)的使用极大地改善了我们预测和管理疾病的方式,或确定哪些疾病最有可能对特定的治疗产生反应。
目前,在医学领域,没有哪个领域的发展速度能赶上靶向疗法领域的发展速度了。靶向疗法旨在攻击具备独特特征的疾病细胞,同时保护健康细胞。
今天,哈佛医学院的学生入学率还不到4% ,绝对不是文盲。

现代制药业的起源于药剂师和化学公司。药剂师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例如Merck公司,开始进入药品批发生产领域;一些特种化学公司也开始发现自己的产品具有医疗用途。
早期发现药物的一个流行做法是,收集大量化合物,用液化的动物组织测试它们,看看它们粘在哪里。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为“研磨和结合”(grind and bind) ,希望能“发现”( find)。
如果这些化合物中藏着潜在的药物,这肯定是发现它们的一种方法。
随着这种方法变得越来越有成效,我们进入了小分子药物(small molecule medicines)时代,因为这些由科学家制造的化学物质往往足够小,可以口服,而且可以完整地被消化系统吸收。
这些药物一直是历史上最畅销和最受认可的药物,如立普妥(Lipitor)或百忧解(Prozac)。
但并非所有的现代药物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有些疾病是通过注射治疗性蛋白质来治疗的,由于蛋白质的大小和复杂性,这些蛋白质被称为大分子药物(large molecule medicines),例如,为糖尿病患者注射的胰岛素,这是一种通常由胰腺产生的糖调节蛋白质。
从历史上看,像这样的治疗蛋白质必须从天然来源中分离出来;就胰岛素而言,这些主要来源是猪和人的尸体。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重组DNA等技术的进步使科学家们有了想法,也许我们可以插入DNA指令,在细菌或中国仓鼠卵巢(Chinese hamster ovaries)等其他细胞系统中制造蛋白质 ,并诱导它们为我们制造治疗性蛋白质,如胰岛素。
1978年,位于旧金山南部的Genentech公司,在细菌中证明了人类胰岛素的产生,从而迎来了大分子药物的时代。如今,美国十大畅销药物中有七种是大分子药物。
我们现在正处于另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们对什么是医学的观念再次发生转变。我们已经开始超越基于小分子和大分子的药物,转向编程药物(programing medicines),也可以称为是活体药物,主要形式有基因治疗、细胞工程和设计微生物。
这与我们传统的疗法概念大相径庭。大多数分子基础药物通过作用于细胞、DNA或微生物而产生治疗效果。在活体药物的情况下,细胞、DNA或微生物本身就是药物。
现在,编程药物的焦点将从药物的作用机制(药物如何发挥作用)转移到药物采取行动的机制(药物如何思考)。
这些新药本身就是生物,它们将能够感知疾病的存在; 知道遇到疾病时该怎么办; 将自己限制在疾病的部位; 以及在需要停止行动时终止行动。
如果我们要把编程生物学用于医学,需要从源头开始使用生物学自身使用的编程语言。
当DNA的生物“语言”被破坏或变异时,它可能会导致超过7000种已知疾病中的一种,其中大多数会对身体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并且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替换或修复缺陷基因以恢复正常功能一直是这些疾病基因治疗的“圣杯”。
但是当你潜在地永久改变一个人的DNA时,风险是很高的。
几十年来,基因治疗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如何最好地将药物(在这里是基因)输送到患者体内合适的细胞上,以及一旦到位,如何控制基因治疗或编辑的“剂量”以获得期望的效果。
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重大障碍,但它们本身也存在重大风险。挑战依然存在,挫折也比比皆是。
还有一个关于规模的问题:即使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生产足够数量的这些治疗药物也是困难的。
尽管如此,基因治疗的潜力以及CRISPR等新技术应用的兴起也意义重大。
CRISPR是一种基因编辑技术,可以精确地发现和替换DNA。有了它,我们即将改变人类疾病治疗的进程,甚至可能永远改变人类的本质。
我们不仅潜在地改变了我们自身的生物特性,也改变了我们自然对手的生物特性。
如果说医学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对抗微生物入侵者的需要。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个敌人可以成为盟友。
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微生物群,即共生生活在我们每个人体内的丰富的微生物生态系统,实际上是调节一系列健康和疾病状态的关键,从消化、健康到神经系统疾病。
除了健康的微生物群的正常功能外,我们将能够设计微生物来充当“哨兵和士兵”来对抗疾病。
想象一下,将新的基因导入细菌的基因组,这样,一旦细菌被吞下,它就会在你的肠道中繁殖,当它感觉到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的炎症时,就会释放抗炎分子。
如果大肠杆菌或者某些能让我们生病的菌株,可以通过编程使我们变得更好呢?
虽然这听起来有些遥不可及,但一家合成生物学公司正在对几种疾病进行类似的基因工程微生物测试,包括一种名为苯丙酮尿症(PKU)的致命性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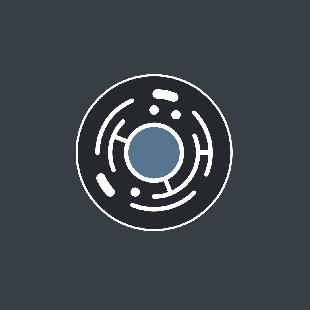
最后,我们开始考虑将人体细胞本身改造成药物的可能性,在过去几年中,这项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工程细胞在对抗古老的人类恶魔癌症方面显示出了特别的希望。
癌细胞有许多邪恶的伎俩,其中之一就是开发逃避免疫系统的方法。
这里的最终目标是训练免疫细胞识别和攻击癌细胞,方法是从患者身上获取免疫细胞,对其进行工程改造,使其对患者自身的癌细胞做出反应,并将工程改造后的细胞送回患者体内。
这种被称为CAR-T的治疗方法,使患者自己的免疫细胞重新编程成为药物。同样,这种方法也有风险,最显著的是免疫反应失控的可能性。
CAR-T疗法也非常昂贵(目前近50万美元) ,生产效率低下,目前只适用于少数类型的癌症(白血病和其他血癌)。
但是,在扩大细胞疗法在其他肿瘤中的应用方面,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投资和创新浪潮。
更大的潜力不仅在于细胞工程,而且在于设计细胞,利用遗传电路作为编程语言的一种形式,向细胞灌输越来越复杂的逻辑,感知疾病,根据环境做出反应,甚至在疾病消除后自行终止。
所有这些,甚至没有涉及到那些不存在于物理世界中的原子,而是存在于比特中的药物。
“数字”疗法的兴起,我们正在使用编程软件的形式开发药物,从治疗糖尿病到药物滥用,从抑郁症到多动症。这些“药物”使我们能够通过行为修正来治疗复杂的疾病,而针对特定生物途径的单个分子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随着我们关于药物构成的集体概念不断演变,监管机构也在不断适应。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宣布了额外的精简措施,以确保某些基因疗法、癌症药物和非专利药物能够更快地到达病人手中。
2017年对于新药物和新疗法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因为我们看到第一个基因、工程细胞和数字化疗法获得批准,许多都是由FDA小组一致推荐的。
2018年,FDA创下了新纪录,批准了59种新型药物和生物制剂。 该机构甚至宣布了一项监管方针,以鼓励在医学领域使用人工智能算法。
从本质上讲,这种算法将为我们提供第一批药物,而这些药物本身会随着我们的身体状况好转而变得更好。
这些新药究竟如何销售,如何支付,如何大规模地进入病人的手中,这些问题仍然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解决。
所有这些新药都将是昂贵的;毫无疑问,第一种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药物即将问世。
但是这些药物对于接受它们的患者来说是真正的变革,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接近了医学上一直难以实现的首要目标:治愈。
保险公司,甚至制药公司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巨大的转变,并开始尝试新的模式:从按药丸付费的模式转向按治愈率付费的模式,甚至可能是分期付款的模式,购买药物实质上是订阅你的新基因或人工细胞。
有朝一日,我们可能会看到药物领域的Netflix出现,这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制药是一个漫长、危险和昂贵的过程。
毫无疑问,编程药物已经并将继续面临独特的挑战和挫折。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转折点上,医学的意义不仅被分解成新的工具,而且被分解成新的模式和类别。
随着我们日益走向充满编程药物的社会,这些药物——基因、细胞、微生物——将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也会反过来重新建构我们自己。
原文链接:https://a16z.com/2019/02/07/what-is-a-medicine-jorge-conde/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