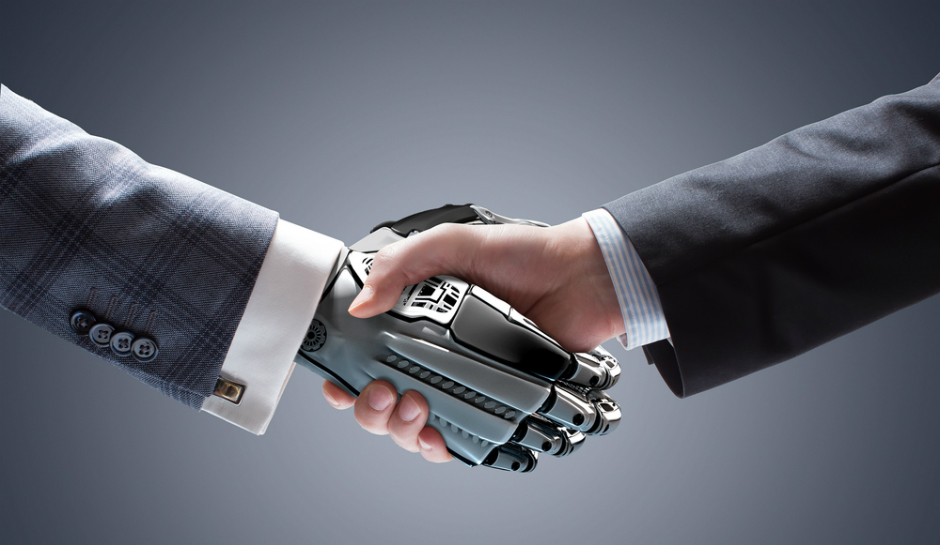AI 将成为你的同事,可你愿意跟它们一起工作吗?
编者按:AI会识别图像语音甚至下围棋似乎对我们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是随着AI在工作自动化中的渗透,我们的饭碗会不会丢掉呢?《连线》杂志的一篇文章聚焦了翻译、律师、新闻、电影等行业的AI应用现状,提出现在AI不进没有威胁到我们的工作,甚至还能促进我们的生产力。但是,就像银行出纳员在ATM出现后一度增长最后又开始慢慢减少的传奇故事一样,短时间内是我们友好同事的AI有朝一日就会变成抢走我们饭碗的可怕妖怪。
去年秋天,Google翻译推出了新的改进版的人工智能翻译引擎,公司在当时宣称其效果“几乎与人类翻译别无二致”。Jost Zetzsche对此的反应只有翻白眼。这位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从事专业翻译已经有20年,在此期间他时不时会听到自己的行业会受到自动化进展威胁的言论。但每一次他都发现炒作总是言过其实——Google翻译这次所谓的升级也不例外。所以他想,这一定不是翻译的关键。
但Google翻译出奇的好。2016年Google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用AI来改造它的翻译工具——为此,Google做出一件强大得令人紧张的东西来。Google Translate,翻译只能说过得去但是不流畅的工具,开始能生成流利且高度精确的句子。在没有经过训练的人看来,这种输出几乎与人类翻译毫无区别。《纽约时报》的万字长文称赞它是“伟大AI的觉醒”。这个引擎迅速学会了新的技巧,想出了如何翻译自己未曾见过的语言对的办法:如果它可以把英语变成日语,并且把英语变成韩语的话,那就可以把韩文翻译成日语。上个月Pixel 2发布的时候,Google把它那雄心勃勃的计划有往前推进了一步,引入有望实时翻译40种语言的无线耳机。
自从IBM在1954年首次推出先驱性质的机器翻译以来,无瑕疵机器翻译的想法就抓住了程序员以及大众之流的想象。科幻小说作家利用了这个想法,构思出从《星际迷航》的宇宙翻译器到《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的巴别鱼的一系列乌托邦愿景。人类水准的翻译——能够捕捉源文字意思的流利表述——是机器学习的圣杯:这是“AI完备性”的挑战之一,如果能征服它的话,将意味着机器达到了人类的智能水平。对Google在神经机器翻译取得进展的炫耀意味着圣杯已经触手可及——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工人变得过时的那一刻将要来到。
但翻译员一直以来都处在AI诱发的就业恐慌的前沿,对此他们并不担心。实际上,有的还挺高兴的。队员写抓住了AI工具潜能的人来说,生产力反而突飞猛进,同样如此的还有对他们工作的需求。
可以把他们想象成是白领矿井里面的金丝雀。此刻,他们还在歌唱。随着深度学习的迅速发展,许多行业正在着手应对这个事实,即AI的确适合一些一度被认为只有人才能胜任的任务。跟司机和仓库管理员不同,知识型员工不会立即面临被替代的危险。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成为其工作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工作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并不能保证今天起到帮助作用的AI工具将来不会变成威胁。这就迫使员工们要做出选择:要么放下你的自负,拥抱你新的AI同事,要么被淘汰。
我们还没有生活在AI的黄金时代,但我们生活在AI增强生产力的黄金时代。姑且称之为首关时代(First Pass Era)。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强大到可以对无数的复杂任务进行首次尝试,但是它还没有强大到对人构成威胁的地步。对于更为思维密集型的主观工作而言,我们仍然需要人类。
这一劳动力转移正在各行各业展开。去年《华盛顿邮报》自研的AI Heliograf写了大约850个故事,人类记者和编辑在此基础再添加上分析和生动的细节。在平面设计领域,AI工具现在可以生成设计的初稿,再把最后的实施交给人类设计师。在电影和出版业,新的工具有望在废稿堆中撬出下一部流行作品,把编辑从通过粘贴堆杂草来寻找下一个巨大的命中,从编辑永不停歇的作品提交队列中解放出来。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就像打了兴奋剂的年轻无畏的助手一样,他们极其能干而且高产,但仍然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经理来承担繁重的脑力活。当然,这位经理必须跟机器一起工作才能得到那些好处。
在亚利桑那州的律师事务所Fennemore Craig,那里的律师就已经跳上了这趟AI列车,他们试用了一家名为ROSS Intelligence的初创企业的新技术。ROSS采用了IBM Watson以及专有算法,属于LexisNexis这样的工具的AI驱动型后继者:它会对数百万页的判例法进行梳理,并把自己的发现记录在草案备忘录上。这个过程一般需要人类律师4天的时间,而ROSS大约只需要24小时。而且ROSS不会受精疲力竭或者油尽灯枯之困:这项工具可以无数个晚上挑灯夜战而不会备受磨难。
ROSS的写作能力尽管可以一用,但并不是它的突出特点。按照Fennemore Craig 3年的准合伙人Blake Atkinson的说法,其写作水平大约相当于一年级法律学生的水平。(公司合伙人Anthony Austin的评价则要更大方一点:在他看来,ROSS已经跟一些第1年或者第2年的准合伙人水平相当)。该工具可以生成整洁的备忘录,尽管没有海明威水平那么高,但它提供了一份功能优先的初稿,里面填上了各种适用判例法的摘要,还进行了一些基本的分析,并且给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结论。人类律师然后在补充进一步的分析并对文字进行润色,令文字读起来可以很享受——至少对律师来说如此。Austin说:“这可以让我们得到生动有趣的东西。 就好比说,‘我的老天爷啊,我才不关心1885年的蒸汽机呢,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写点有趣的、吸引人东西,有趣到法官或反方律师会认为,我的妈呀,我死定了。’”
到头来,像ROSS这样的工具几乎肯定会减少在取证过程中对人类律师的需求。目前尚不清楚这将如何改变入门级律师的用工情况,后者的工作通常是在闲暇时间对旧的判例进行艰苦的梳理。但是深入的分析和有吸引力的写作仍然远远超出ROSS的能力范围。律师不害怕ROSS对这家初创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毕竟嘛,谁愿意去培训会取代自己的“人”呢?这就是为什么公司CEO Andrew Arruda把ROSS当成是生产力工具而不是AI律师来兜售的原因;它让律师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让他们可以专注于自身工作中的有趣部分。Austin说得更加言简意赅:他说,在ROSS的帮助下:“你看起来就像一位摇滚明星。
对于许多翻译人员来说,有AI助力的超人般的超高生产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03年,Alessandro Cattelan在开始他的翻译生涯时,他的期望是每天翻译2000字,挣到大约175美元。他利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基于他之前的工作为某个短语偶尔提供一些建议——但翻译是一个非常人工的过程。而今天,Cattelan说,在人工智能的协同工作下,同样的一笔钱(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翻译人员现在一天可以翻译8000到1万字。这个过程被称为机器翻译后编辑(PEMT),着牵涉到首先让机器过一遍,然后再由翻译人员来整理语言,检查解释不正确的术语,同时确保翻译的语气、上下文以及文化线索都比较到位。
现为AI翻译工具Translated运营副总裁的Cattelan说:“你必须弄清楚自己工作中哪些地方可以由机器替代,哪些地方是你作为一个人能够带来价值的。”自从今年4月份Translated开始向译后编辑提供神经机器翻译以来,其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像德语和俄语等由于语法复杂过去往往需要额外调整的语言提升尤其显著。
PEMT不是什么新东西——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小众领域就一直在不断发展,但是随着神经机器翻译的出现,它正得到更为广泛的采用。根据市场调研公司Common Sense Advisory的数据,未来几年对译后编辑的需求增长速度预计将比语言行业其他任何板块都要快,未来几年企业翻译可能会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Common Sense Advisory警告说,“即使语言行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新的翻译人员,目前的方法也不可能跟上这种增长水平”。有人说,跟机器翻译合作已经成为强制要求:根据机器辅助翻译平台Lilt的CEO Spence Green说,“机器翻译”现在已经成为必需,而对于老一点的翻译人员来说,他们甚至都不需要使用翻译记忆软件了。
住在悉尼的翻译Charlotte Brasler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机器翻译工具已经变得好到除非她使用这些工具会破坏保密协议(时有发生的障碍),否则的话她倾向于借助工具来翻译。与超级能干的AI一起工作让她能够承接更多的项目,并且腾出时间以便能够处理更需要创意的文字,那是机器过去无法翻译的。
但是哪怕是这一点也在发生变化:Brasler说,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神经网络的加入,Google Translate在处理销售和营销材料方面已经表现得出色,这方面的翻译已经牵涉到生动语言的使用和对习语的解释。当然,引擎还不是诗人,但在大家一直以为机器不可能征服的领域,它正在迅速改进自己。对于那些靠自身手艺来定义自己的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技术的飞跃永远会遭到抵抗。会有人无法忍受跟机器合作的想法,还有人宁愿把自己当作鸵鸟把头埋进自己的想法日记里面,假装什么也没有改变。对于这些工作者来说,这种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无异于是一场生存危机。当然,计算可以筛选数据,甚至可以拼凑一个基本的句子——但它能写出会让你流泪的散文吗?它能分析一条成语的玄妙之处吗?或者发掘下一位畅销书作家吗?它能说服最高法院的法官来改变想法吗?
还不行,但它可以帮你做到这些。随着一些最需要创意的行业开始尝试人工智能,他们正在面临一些阻拦。今年四月,The Black List(电影制片人和编剧的关系网络)宣布将与一家名为ScriptBook的人工智能公司合作评估一些剧本,后者可以对剧本进行角色分析、识别目标人群、预测票房成功率等,但作家可就不干了。 《亿万》的执行制作人Brian Koppelman称这种工具“粗鄙且令人作呕”。The Black List很快就取消了与ScriptBook的合作关系。虽然该初创企业已经与两家主要的电影工作室成功合作,但ScriptBook的CEO Nadira Azermai表示,大多数电影制片人还没有能够克服对这个工具的恐惧。
Azermai 说:“几年前,大家还认为在创意领域我们是安全的,因为人工智能没法变得像人类一样具有创造性,或者没有人类那么特别。这是不对的。”当业内人士指责她创造了一个工具来偷走他们的工作时,她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工作确实受到了威胁,但威胁他们的并不是AI。相反,她对反对者说:“你会失去工作给那些学会了如何如何跟机器合作的人。如果你总是把头扭到一边假装它不存在的话,你就会丢掉饭碗。”
另一个类似的工具是StoryFit,其功能包括票房预测,剧本结构和风格分析以及故事情感元素的解读。正如TJ Barrack的解释那样,他的工作室Adaptive Studios绝对不会仅仅因为在StoryFit的报告中看到某样东西而通过一份剧本——但是他的团队可能会考虑如何基于它了解到的东西来对剧本进行改编。 Barrack说:“如果它告诉我说基于这些特定的东西作品上市可能会遇到问题的话,故事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改进一下的呢? 有哪些情节可以调正一下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或那儿添加更多的情感因素进去吗?”
大家刚刚开始摆脱人工智能的炒作,开始专注于AI驱动工具可以如何帮助自己的工作。StoryFit CEO Monica Landers表示,她最近开始看到对自己公司产品的担忧正在消失。但她仍然需要小心行事。在被问到公司接下来要怎么做时,她的回答有点犹豫不决:“这件事情如果说得太早的话又会有人开始要紧张了。”
那么这就可以理解了:如果我们放弃人类特有的创造力和直觉的话,我们首先就必须彻底反思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两种技能都暗示着某种不可知的想象力或第六感。但事实上,机器已经很有创造力,能够制作出令人惊讶的创新性的艺术作品:它们可以拍照,会写音乐,能创作出可与达利一决高下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只是当它们开始能够以一种令人类产生深深共鸣的方式做这些事情时我们才需要担心。
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主算法》一书的作者Pedro Domingos说:“机器是可以有创造性的,而且它们其实已经有创造力。”不过直觉则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直觉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人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技术界最好的工程师还没有想出如何让AI具备直觉;只要这种情况延续下去,人类就能在工作中占据上风。律师需要了解她的目标受众以及此人可能存在的所有偏见或者倾向;译者需要对他所翻译的两种文化有细致入微的理解。Domingos说:“只要这些任务中的一个投入到现实世界里面,机器就会落后,而人确实具有优势——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此。”
有了我们的AI同事之后,工作开始看起来像是乌托邦里面的样子。机器接管了直到最近还太过复杂而不能自动化的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任务,让人类可以沉浸到工作中最有创意和最有价值的地方。但是,这种模式我们之前也曾经见过——最终会走下破灭的一股热潮。
在1960年代末首次推出ATM时,很多人都惊讶地看到美国的银行出纳员人数反而增加了一倍,并且数十年都在一直增长。在从枯燥的点钞工作中解放出来后,银行职员就可以把她们的注意力转向帮助客户解决账户问题或给收银员开具发票上;这样一来她们就变得更有生产力了。但是,经过那一轮增长之后,现在银行职员的数量正在下降,这是由于PayPal、手机银行等技术的累积效应,以及对现金需求的下降。这个过程花费了一段时间,但技术终于从对我们的恩惠摇身一变为妖魔鬼怪。在MIT 数字经济项目(Initiative on the Digital Economy)联合主任Andrew McAfee看来,银行出纳员的传奇故事是一个警世寓言。他说:“如果说技术在一段时间内会增强工作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话,那并不意味着它一直都会如此。这出戏我们以前就看过。”
不过到目前为止,翻译人员、律师、医生、记者以及出版经纪人的工作还是安全的。有人甚至会说自己的就业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但我们现在的确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我们必须承认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掌握一直以来被视为机器禁区的任务。我们必须认识到,拥抱AI正在迅速成为在许多领域鹤立鸡群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欢迎这些新的AI同事,并且在它们犯错的时候纠正他们——同时我们还得承认,到了某个时候,当我们已经教会它们足够多的东西时,AI就能开始顺着职位晋升的梯子往上爬。
原文链接:https://www.wired.com/story/welcome-to-the-era-of-the-ai-coworker/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