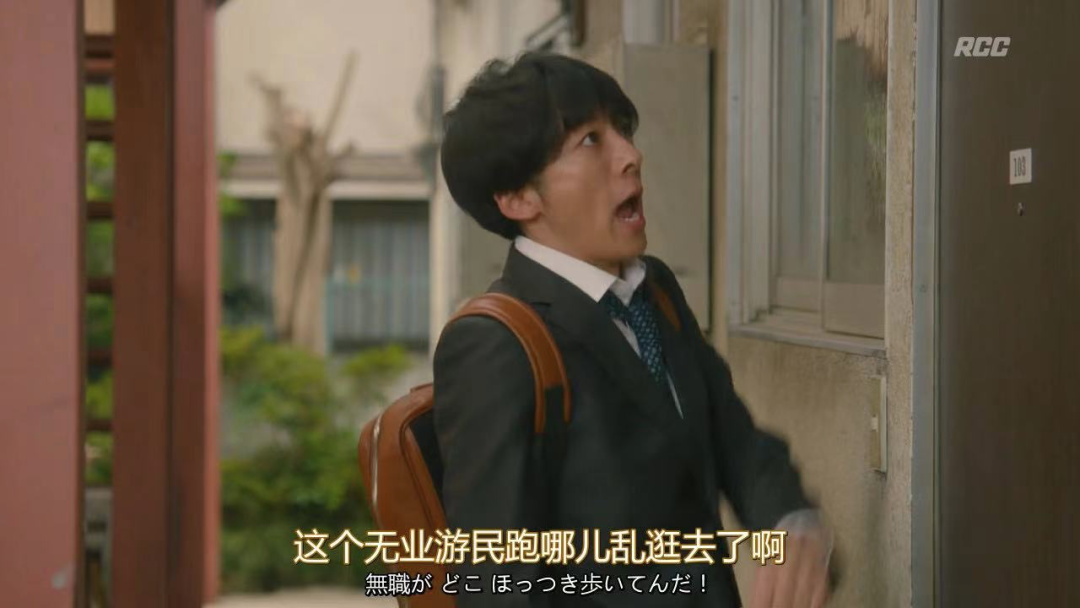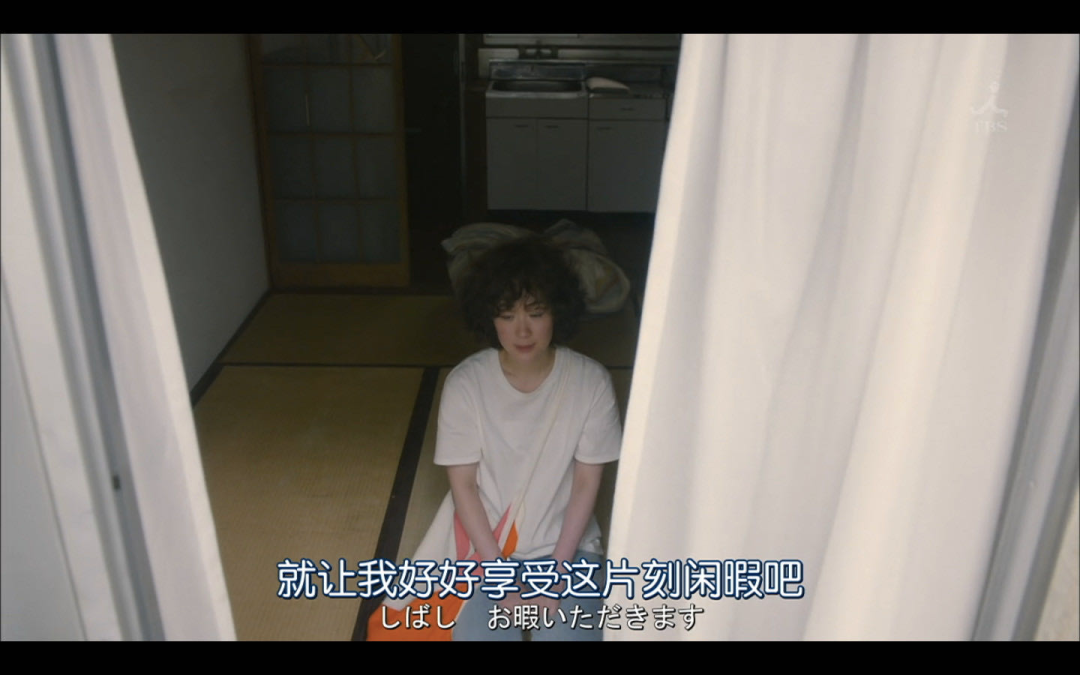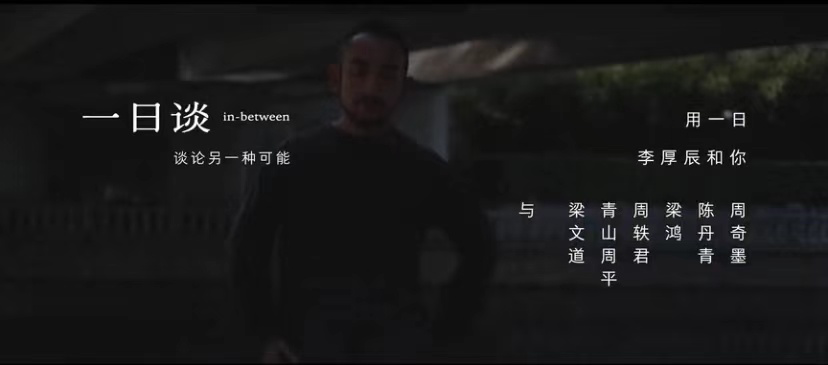我们为什么抱怨工作,感到被剥削?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没有 KPI 的,36氪经授权发布。
本期嘉宾
■ 李厚辰:“翻转电台”主播、“看理想”平台《李想主义》专栏作者、《一日谈》主持人。
春节假期过后,我们问李厚辰,为什么我们觉得假期一终止,快乐就结束了?
李厚辰说,过去的“节日”要么是宗教祭祀,要么是权力庆典,要么是极端义务开始之前的放纵,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狂欢节”都是斋月的开始。人们“庆贺”不是为了自己,节日中人们有很多“义务”劳动的。“假期”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是“自己节”、“消费节”、“无义务节”。“假期”成为了“平庸化的狂欢”,大家往往也没有多么放纵,顶多就是懒散和放松,即丧失了祭祀节庆的“目的”,也丧失了狂欢节庆的放肆。更像是监狱的“放风”,一种难得的喘息之机。
编辑部感慨小李老师又一针见血了。上一回,李厚辰和我们聊了《这个时代对年轻人真的很“坏”吗》他谈到“内卷”和“异化”概念,可能成为新的“教条”,谈到我们要反思“个人主义”,谈到良好生活的实践起点。我们太受益匪浅,于是几个月来持续在发问“工作”和“996”的我们,再一次找到李厚辰,请他谈谈对工作的看法。
- 工作里真正让我们觉得痛苦的是什么?
李厚辰住在上海梧桐区的一个老居民小区里,没有逼仄的高楼,环境日常而松散。走到一栋旧式单元楼前,哔哔哔一把电子锁打开,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屋内窗明几净,有一整面墙的书、一把大提琴,还有一只长长的惠比特猎犬正窝在沙发上。我们席地而坐,对话也就此展开。李厚辰谈到他选择“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生活时,摊开双手说,“你们看我也没有过的很糟糕啊是吧”。
李厚辰的工作和生活“其实很简单”,九点起床,下午一点午休,工作到晚上十二点睡觉。吃饭自己做,每天遛两次狗,闲暇时会练练琴,做做运动,看个电影,吃饭的时候也会看看 Youtube。闲暇的时间非常少,但他却觉得工作得挺来劲。他做过很多工作,从高薪的咨询顾问、到互联网公司、后来互联网创业,现在做自媒体,下一步想做教育。这样一个人,周游了一圈最后选择了自媒体和教育,这其中必然经历了选择。于是,我们也请他谈了谈自己的几段经历。
李厚辰:
为什么我们会抱怨工作、感到“被剥削”?
我看过你们关于工作的访谈(编辑注:我们把这篇文章所涉及的采访资料发给了李厚辰),特别有意思。其中对工作满意度最高的两个人,其实是大众看来工作阶层最低的人:一个是星巴克实习生,一个是推拿师傅。从所谓“剥削”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是被剥削的最厉害的 —— 实习生的工资极低,推拿师傅算是社会工作阶层较低的一种职业,但他们的工作满意程度却是最高的。而另外一群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人,拿着比较高的收入,给工作的满意度打分却都是将将及格或者在及格线以下。
这是没办法用「劳动剥削理论」去合理解释的。从劳动剥削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应该是被剥削的最严重的。马克思理论没法很好的解释的一个原因,是在工作中和其他人的关系,尤其是与老板的关系:不满意不是因为钱被剥削,而是由于职场 PUA。这在阿伦特「劳动-工作-行动」的三分法里解释得比较完整 ——职场 PUA 不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一种剥削关系,它本身是对「行动价值」的剥夺。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谈到了人的三种基本活动:劳动(Labor),工作 (Work)和行动 (Action)。(编辑注:敲下黑板。小李老师后面反复提及这个框架中的“行动”。)
劳动的意思很简单,我们每个人要维持自然生存,就需要劳动。比如说我在家做饭、给狗做饭,本质上就是一种劳动,一个家庭里就存在许多劳动。
工作是指,社会存在分工,比如说我为了维持生存,家里自来水管拧开就要出水,水管坏了也得有人修,修水管就是一份工作。工作和维系生物体生存不直接相关,说个简单的例子,在这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有一部手机,但手机跟生存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没有手机也能够生存,但是你离了它就没法跟社会来进行分工协作,所以手机就变成一个工作属性非常强的东西。
第三个叫行动,行动是能够以自己的想法来改变他人的生活形式、或者给他人赋予一种良好生活的、具有政治性的行为。“政治性”不一定是宏观的巨大的东西。政治性在于,在家庭之外,促使他人以你对生活的理解来生活。所以一群朋友一起玩,仅仅是玩伴,没有政治性。但一群朋友一起聊天,其中一个人侃侃而谈,大家开始倾听和认可他,进而影响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行动”。
你们访谈调查中的年轻人,他们中一些人对老板的抱怨,实际上是在于对他意见的不尊重,或者强迫他要去做一些什么事。这是对工作中的“行动”的剥夺。
譬如一个在互联网大厂的信息安全师,由于要依照公司和老板的规划不断地去优先做紧急的项目,而无法通过做感兴趣的项目来实现自己的技术理想,在这个场景去理解“剥削”,在于 TA 的行动变成了他人行动意志的一部分。这种行动价值的剥削也体现在甲方对乙方的关系中。像在会计审计、广告、建筑设计、商业咨询这些高薪、同时也是知识经济和知识生产上非常前沿的行业里,依然有很多人抱怨对工作的不爽 —— “你找我来,我的意见你还不接受,还瞎改一版两版三版的”。
这些情况就很难用马克思的理论去理解,因为这钱给的足够,甲方要求修改有什么不行的。马克思所强调的剥削是在劳动成果分配,即生产意义上的剥削,一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为了别人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但在这里,是一种「行动价值」的剥削,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有行动的意愿,现在却成为了别人的行动意志的一部分。同时意味着,行动价值被剥夺也许比财务收益被剥夺更让人难受。
对于都市白领阶层来说,我们在劳动上被剥削得都还不算惨。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我们还算是“半既得利益阶层”,真正惨的是每天维持着我们这种生活运转的人,比如为我们提供手机的富士康工人、外卖送餐员、地铁安检员,他们从事大量重复、枯燥的工作换得平平的薪水,这个才是真的劳动剥削。
总的来说,我觉得很多人工作得不爽,更多是因为在工作中他的“行动”的丧失。
星巴克实习生和推拿师傅,对于工作的满意度会更高,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没有什么行动要素需要考虑。在星巴克,客人买杯咖啡,做好就走。客人告诉推拿师傅哪里不舒服后按他的方法按,基本也会按完就走。而公司里的人,原本有“行动”的期待,就会感到被剥夺。
©《不求上进的玉子》
我们和老板之间的矛盾究竟出现在哪里?
造成“行动价值”被剥削感的原因,一是大企业多是高度计划式的管理体制,员工不得不按照计划执行。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都是计划经济体,在企业内部的层级结构之中,每年的计划预算会分到每个部门。这种“理性铁笼”的结构,容易导致被临时调换部门,或者在做的事突然砍了不做了,项目也因此难以推进。比如拼多多事件中一个过世的女生,她被临时调到新疆去做社区团购,就是由于这是大企业计划进行中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个人能改变的空间是很有限的。
二是 KPI,在工作领域,阿伦特认为真正的危机是彻底的功利主义化。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被流量的 KPI 绑架,但 KPI 不是由我们来制定的,我们只是为赚钱这种功利主义服务。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我们和老板的矛盾,就来自于老板是 KPI 的制定者和裁判。他同时有权力给我们打分评级,决定升迁和年终奖。在这种权力关系中,我们又总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解决的路径的,譬如去抵制这种工作层级的功利主义化。这可能跟每个人生活和他的消费结构也有关系。尤其是有选择权的人。有时候一个人的支出和财务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在决定着,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这跟每个人的物欲还是有挺大关系的一个事。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工作的完整感愈加缺失?
今天的社会分工分的越来越细,处于流程中间的职业越来越多,工作的完整感愈加缺失。很多人离他的行动结果非常远,只能间接地认为自己做的事在推动行动,但没有任何实感,不产生任何的实际经验,没有看到它到底带来什么效果。
比如,公司里的程序员、后台做数据的人只是面对一台电脑,外卖送餐员东西放在那里就走……这些工作远离直接的人,接触的就是数字。但最终业绩的数字不产生“经验”,因为人的经验还是需要调动感官和认知框架去理解的东西,它不光光是一个数值。因此,这样的工作会让他没有行动的感觉,也会让他觉得跟结果离得特别远。
但这样“被价值剥削”的情况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单一家庭自足”在现今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必然互相依赖。而参与到社会分工和协作,就产生了“工作”和“行动”,也就产生了权力和支配,不平等必然就会产生。
我们必然面对一个问题:不管是“利益”的分配,还是“行动价值”的分配,都存在剥削。假如我们今天先不讨论利益的分配,而讨论行动价值的分配,我们怎么让行动价值的分配变得更好?
如果你有幸拥有了“行动价值”,要想办法把它分享出去。
如果我现在确实疯狂占有某个行动价值,这个行动价值又不是独立完成的,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我能如何把这个价值让更多人分享?
对于做电台的人来讲,如果能在评论区几乎回复每一条评论,这更容易把对方拉入到对话中来,让对方也得到了回应。我做了个问答的栏目,让听众的想法能够在台面上呈现、反映出来。这些作法让行动的价值不完全由自己一个人占有。行动价值跟钱不一样,不是你占有了我就没有了。
获取“行动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主动寻求和他人的直接接触。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工作处在一个中间环节之上,跟上跟下都不接触。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主动寻求和他人的直接接触。
像很多今天在城市里工作中的人,他们都有一种职业终结点的梦想,我管它叫“开三馆” —— 餐馆、咖啡馆、瑜伽馆。很多人想,“如果我赚够钱了,我就开一个”。开“三馆”和开别的不一样,在城市里,餐馆、咖啡馆、瑜伽馆,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在追求跟其他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因为这份工作没有那么多中间环节,你能跟你的客人直接接触。而且在这个空间内,你能相当完整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开餐馆、咖啡馆、瑜伽馆更具有我们所说的“行动价值”。所以这种工作变得很有魅力,让人们很向往。
不滥用技术性的工具,也是一种调节的方式。现代社会,我们用各种技术性工具辅助我们的工作,但技术性工具用得越多,行动很可能被削弱得越厉害。因为所有技术都是促使你能跟其他人中间再隔一层。听说钉钉马上要推出一个校园版,用于老师、学生和家长的沟通,老师的行动价值感可能很大程度上会被钉钉这样的软件弱化。我也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微信群是如何把老师跟家长的关系彻底搞坏的。技术性工具可能带来效率,但不一定带来非常好的(行动)效果。
我说一个我的例子。我每次活动拉群和解散群,其实不会花非常多的时间,但每次还是坐在那半个小时,全在机械地点击。很多人跟我说,有那么多拉群工具能一键拉群,你干嘛呢。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确实每次点半个小时拉群,都能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能发现谁又来了,谁怎么还没报名。这必须在传统工业者的生产形态之下才会浮现的。
也就是说,今天的很多工具在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高效,但是是否要用这些工具,很大程度是我们需要从在意的“行动价值”中要考虑的。很多时候,我们一旦选择了使用工具,行动价值就会被拿走一部分。
在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行动价值。
这还是与一个人的选择有关。
大互联网公司在意拉新、维持日活来实现 KPI,沦为功利主义剥夺了人们的行动价值,但我们很难让他们改变。这与他们的股票直接挂钩,背后是上百亿、上千亿的利润。
但还有很多公益机构或者组织,他们主要在意两个部分。一是收支平衡,要做到生存。另一部分就不靠数量型的 KPI 完成了,就可以考虑好多别的事情。就像一个面馆老板,他爱做面的话,也是会考虑收支平衡、让生活得以继续。另一部分则是去想怎么能做出更好吃的面。
虽然不能把工作二分法为“收支平衡型”工作和“利润无限大型“工作,但还是存在中间点的。有些公司既坚固利润和发展,但也不会完全服务于 KPI。假如你选择了一家上市公司,它基本追求的就是利润无限大,那么这家上市公司就会受到投资人、股市上下涨幅等影响,不是你能左右的。在这个逻辑之下服务于这家公司,行动价值就很难去保全。
我们觉得好像不能10年做到年薪百万,就会崩溃了。其实不会的。
我们对闲暇的想象就是消费。绝大多数人满足不了充分消费,但是今天的社会景观却是被极少数充分消费者塑造的。在商业广告里,家都是那样的家,车都是那样的车,男士都是笔挺的定制西装……我们的现实生活显然并不是那样的,但这样的消费图景足以让人因自身的匮乏而焦虑。
为了实现那样充分消费的图景,我们有时会甘愿选择“行动价值被剥削”的工作,把工作完全功利主义化,把工作和闲暇分得很开。闲暇的标志就是去消费,有了社交网络之后,我们的闲暇更是要被呈现出来。比如我去了国外,那得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展示我是一个充分消费者。
现在的人把闲暇当成一个消费的对象,好像你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另外一个东西(闲暇)做准备,工作时肯定是不享受的,心理肯定压力是大的。
“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媒体总是报道大成功和大失败,塑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你不高速增长,你就活不下去。我们觉得好像我要是不10年赚到年薪100万,到时候就会崩溃了。其实不会的。对吧?实际上,你关注你身边的企业、沿街的店铺,绝大多数人仅是处于一种收支平衡的状态,满足了收支平衡的生活就不会崩溃,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你才能有闲心来考虑赚钱之外的事。
接受了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生活,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选择。比如你如果去做公益咨询,就不要指望能够拿到麦肯锡咨询咨询顾问的工资的80%,而是接受麦肯锡工资的40%。
当然,这和个人选择有关,你要是想要拿30个月的年终奖,仅仅靠收支平衡的工作方式,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每天工作五小时,年收入百万?没有这样的好事。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赚这么多钱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消费是有必要的吗?
对我来说,我已经35岁了,每年就赚那么多钱。但其实我的生活条件也不错,在上海住这么一房子,养着一只狗,每天工作干得挺起劲。我的快乐和享受并不必须依靠消费完成,我可以关注身边的人、狗,我对他们有责任,要去陪伴他们,而他们也会带给我生活的实感,所以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并不需要依靠充分消费获得。
或者,你也可以参与到某种更具公共性的事物中,比如说一个女权主义者,对他/她的生活讲,可能充分消费就没那么重要。为什么这样的人消费欲望会比较低?因为他们可以不通过消费来完善自我、不通过消费来定义自我,他的自我价值在其他地方得到了很大的完善,所以这种人并不是非要去充分消费。
李厚辰的工作经历:互联网创业是最浪费时间的两年
我做过很多工作,让我有行动价值感的好工作没有几份。早年,我在咨询公司,工作结果离实际的成果非常遥远。在网上搜行业、做访问,成为了 PPT 表演艺术家,好像提了一些意见,但其实最后的结果又跟我没什么关系。现在回想,这份工作对我的个人成长、增长见识有些帮助。但让我不满意的是,我会觉得好像我做啥了,又好像啥也没做。
互联网这块,我既在豆瓣工作过,也自己创业过。在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做的事情会有意思一些,因为你能看到实际的影响和反馈。但后来我还是会觉得,比起实际的写书、做音乐、拍电影,你做一个平台让别人去评价一下,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做平台,一个直接的比喻就是,搭台给别人唱戏,但实际上更有行动价值的事,确实还是唱戏本身。
我自己后来也做了一个平台型的创业项目,是一个社会实验——“享借”(建立在人与人信任基础之上的物品共享平台)。似乎是想从这个世界之外,建立一个封闭性的秩序,在封闭性的秩序里面是美好的,但后来发现行不通。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被流量、KPI绑架。互联网创业的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浪费时间的几年,除了最后逼着我学会了编程,其它并没有什么别的成长。
曾经我们以为互联网平台可以改变世界。滴滴、共享单车,最开始都这么说,最后啥也没改变。淘宝也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但现在生意反而是越来越难做了,光是玩转淘宝本身的规则就已经够难的了。我也不再相信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我觉得有行动价值的事还是要靠潜移默化地从细节处、积累性地来做,最理想的状态是实现了工作、行动的合一化,这样即使每天都在重复地做一类事,你也会觉得工作得很带劲儿。我接下来想做教育的事,潜移默化的来做。
李厚辰对于闲暇的实践:相比于热衷户外期间我看到的美景,估计我死之前想我做电台的事情可能还多一点。
早期我在咨询公司做的时候,确实是由于工作结果离实际的成果非常遥远,我那会儿的闲暇基本上是以消费和自我扩展为主的。那段时间基本与我玩户外的时候是重合的。我每个周末去远一点的地方爬山,没什么别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是人生中留下的一些美好回忆。但是你说户外的经历对我有多重要呢?也没那么重要。我死之前会想起我看到的风景吗?估计不会。估计我死之前想我做电台的事情可能还多一点。
在豆瓣工作的时候,闲暇时间非常多。当时豆瓣才几十个人,我们早上11点去下午5点走。那段时间就是谈恋爱,所以花在劳动上的时间非常多,比如做饭,但劳动也挺好的。对我来说闲暇时间谈恋爱的这段和户外比较的话,那还是谈恋爱好哈哈。
我后来创业,体验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生活形式 —— 没闲暇,功利主义的事物把我占满了,为了以后可以融资、被收购、上市、一口气财务自由,或者,为了下轮融资。当时工作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为了增长日活的事情,意义非常小。互联网创业那几年是我认为人生中最浪费时间的几年,它给予我自己的成长说实话非常少。
李厚辰主持的「一日谈」栏目,与陈丹青、梁文道、青山周平等六位当代文化艺术领域的思想者探讨今日「良好生活」的可能。©《一日谈》
现在我的生活中工作时间非常长,都在做发展电台相关的各种事情,但还挺起劲的。我基本上从睁眼到晚上12点都在工作。中间除了带狗狗出去玩,其他所有时间都在工作。这个工作就与行动高度合一,我过的是一个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生活。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对自己的工作价值还是很满意的。我用现在这个方式创作,绝对不是因为我现在流量稍微有一点影响力,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十几个人听。中间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接一些咨询的私活,为我生活上的收支平衡提供一个补充。
所以我会觉得有很多生活内核是靠你自己去完成自足的,包括你养的植物,你的孩子,你的狗狗等等,而不是靠钱和消费来维持。这部分会给我们一些安全感,并且对一个人去做的生活选择也挺重要的。他能有能力去安排生活,完成自己闲暇时间的娱乐。我们谈恋爱也是认为能有多一个人把他引入到这种生活形式中来,而不是每个周末都需要靠消费。如果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下午干什么、晚上干什么,都需要靠消费填充的话,以后压力会变得很大。当你自己能够完成的话,就会好一些。
©《一日谈》
篇幅所限,还有很多精彩的对话无法在文章中呈现。在音频中(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你还会听到李厚辰、和青年志伙伴谈们到的更多话题:
- 企业的“增长神话”已经影响了个人财富的“增长神话”
- “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同样剥夺了人的行动价值
- 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对有孩子的个人情况来说可行吗?
-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企业,他们不仅收支平衡过得挺带劲,而且践行着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
- 只有自由职业的工作才是好的工作吗?
- 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有安全感?
- 我们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担忧怎么办?
采访 | 李颐、张安定
编辑 | 沐雪、Sharon
设计 | Sam
图片 | 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