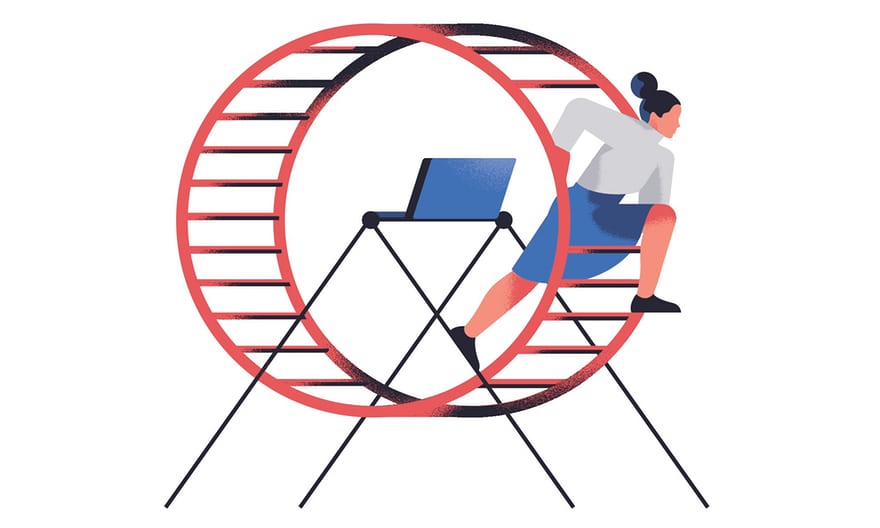漫谈“后工作时代”: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
(一)
工作已经统治我们的生活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了,如今这个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但新一代的思想家们坚持认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工作是现代世界的主人。对大多数人来说,无法想象没有工作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在近代历史上,工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彻底地主导和渗透到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尤其在英国和美国更是如此。对就业能力的痴迷贯穿于整个教育系统中。即使是靠领取救济金生活的严重伤残人士也被要求必须是求职者。公司里的超级明星们会炫耀自己被填得满满的工作日程。“努力工作的家庭”会被政客理想化。朋友们会互相展示推销各自的商业想法。科技公司会想法设法让员工相信,全天候24小时工作其实就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零工经济公司声称全天候24小时工作是一种自由。工人们的通勤距离越来越远,罢工次数越来越少,退休时间越来越晚。数字技术已经让工作侵蚀了人们的休闲娱乐时间。
在所有这些相互强化的方式中,工作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并挤出其他因素的影响。正如Joanna Biggs在《All Day Long: A Portrait of Britain at Work》这本书中所写的那样:“在宗教、党派政治和社会团体消失的时候,工作是我们赋予生活意义的方式。”
但是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工作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其实并没有发挥作用。我们拒绝承认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孤立的问题,比如工作在我们的信仰系统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但是工作所带来的失败的证据一直在围绕我们。
作为一种生存和繁荣的来源,现在的工作对于整个社会阶层来说是不够的。在英国,近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约有800万人)都生活在工薪家庭中。在美国,平均工资水平已经停滞了半个世纪之久。
作为社会流动性和自我价值的来源,工作甚至没能让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获得成功。据官方统计数据,在2017年,有一半的英国大学毕业生从事的是那些非大学毕业生就能胜任的职位。“在美国,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对工作的信念正在崩塌,他们已经不指望工作能提升自己满意度或是指望工作能促进社会进步。” 专门研究工作的著名历史学家Benjamin Hunnicutt这样说道。
工作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更多的零时工或短期合同工;更多收入不稳定的个体户;对那些拥有实际工作的的人的公司进行更多的“重组”。作为可持续消费繁荣和大规模住房拥有率的源泉(这是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流经济政策带来的主要成果),工作如今在我们面临的债务和住房危机面前已经名誉扫地了。对很多人来说,不仅仅是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工作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还没有继承财产或者拥有一套房子重要。
不管你是整天都盯着屏幕,还是在销售那些薪资水平过低的人买不起的商品,越来越多的工作感觉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对社会是有害的。美国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在2013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将这些工作称之为“扯淡的工作”。被Graeber 谴责过的工作岗位包括说客、PR研究员、电话销售员、法警和一些辅助产业的岗位(如洗狗员、通晓送披萨的人)。在Graeber看来,这些辅助产业的工作岗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每个人都花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
这一观点似乎有点主观的和粗糙,但却不断得到经济数据的验证。尽管公司在不断地衡量员工的表现,同时在不断强化工作,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变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是员工生产力或者说每小时所产出的价值的增速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在放缓。
毫无疑问,工作越来越被视为是对健康有害的:“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待办事项清单,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卡斯商学院教授Peter Fleming 在他的新书《The Death of Homo Economicus》(经济人的死亡)这样写道,医疗机构开始将这些事情视为与吸烟类似的有害行为。
工作存在严重的分布不均的问题。人们要么工作量太多,要么工作量太少,或在同一个月时间里有时工作量太多有时工作量太少。远离我们不可预测的、消耗一切的工作场所,很多重要的人类活动慢慢被忽视了。工人们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家里的孩子或者年迈的亲人。“工作的危机也是家庭的危机。”社会学家 Helen Hester和Nick Srnicek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老龄化的加剧,这种人类对包括照顾家庭在内的很多重要活动的忽视的现象只会越来越严重。
最终,除了上述说到的所有这些问题和障碍外,现在大家最常讨论的、对工作存亡威胁最大的因素是:自动化和环境问题。最近的一项预测表明,在未来的20年里,人工智能将取代所有人类工作岗位数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其他预测者则怀疑,在一个不断变暖的星球上,工作是否能以目前的有毒形式继续存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就像一个扩张过度的帝国一样,工作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家强大,同时也更加脆弱。我们都知道工作所存在的问题是成倍增加的,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是时候考虑另一种选择了吗?
(二)
我们的工作文化是声称它所存在的缺点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存在,从而来掩盖工作存在的缺点。正如保守党议员Nick Boles在他的新书《Square Deal》中所说的那样:“人类天生就是工作的。” 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长期以来已经内化的一个观点。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个观点的。一些人已经断断续续地表达过将世界从工作中全部或部分解放出来的观点,但是只要现代资本主义继续存在,这点观点就会一直被嘲笑和压制。在未来的愿景中,关于工作更少的承诺一直是非常显著的。1845年,卡尔·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们可以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到那时,他们可以早上打猎,下午捕鱼,晚上蓄养牲畜,晚饭后从事批判。” 1884年,社会主义者William Morris曾这样畅想:未来的工厂是非常漂亮的,工厂周围都是花园,供工人休闲放松,员工们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
1930年,经济学家John Maynard Keynes曾预测,到21世纪初,科技的进步将会将人类带往一个休闲和富足的时代,到那时,人们可以每周只工作15个小时。在1980年,随着被机器人替代的工厂工人越来越多,法国社会和经济理论家André Gorz表示:“废除工作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在未来几十年里,废除工作的方式将成为一个核心的政治议题。”
自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和英国的工作危机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这些异端思想被重新发掘出来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微妙的书籍开始进一步阐述Graeber提出的关于很多工作都是扯淡的工作这样的争论,他们创造了一种快速增长的文学形态,将工作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有时会打上“工作主义”的标签,他们开始探索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工作。一场新的反工作运动已经悄然成形。
Graeber、Hester、Srnicek、Hunnicutt、Fleming和很多其他人是一个松散的、跨越大西洋的思想家网络的成员,他们为西方经济、社会和贫穷国家构想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他们认为,在未来,工作危机、机器人给工作带来的危机和气候变化将会变得变得更加严重。他们将这种未来称为“后工作时代“。
有些作家认为,这样的未来必须包含一个由国家支付给每个工作年龄的人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这是目前关于后工作时代的一个最引人注目和最备受争议的一个观点),这样一来,当自动化时代到来后,他们依然能够生存下去。还有一些人认为,关于UBI的可承受性和道德性的争论会分散人们对更大问题的注意力。
后工作时代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短语,但它提供了巨大的诱人承诺:一种工作量非常少甚至没有工作的生活,一种更平和、更平等、更具公有性、更愉快、更周到、更有政治参与感、更有成就感的生活。简而言之,在后工作时代,人类的很多经验将会被彻底改变。
对很多人来说,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古怪和愚蠢的乐观,而且很可能是不道德的。但是后工作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现在是现实主义者。“要么是自动化,要么是环境,要么是两者的结合将迫使社会对工作的看法发生改变。那么,我们是乌托邦主义者吗?或者乌托邦主义者是那些认为工作将会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的人吗?” 激进的威尔士学者David Frayne这样说道,他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The Refusal of Work》是有关后工作时代的最具说服力的作品之一。
(三)
关于后工作的最佳论点之一是,与传统观点相反,工作意识形态既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自古就有的。“我们所知道的工作是一个最近的构造。” Hunnicutt说道。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Hunnicutt认为我们的工作文化的基石来自于16世纪的新教主义,新教教义认为只有努力劳动才能通向美好的来世;来自于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它需要有纪律的工人和富有动力的企业家;同时来自于20世纪对消费品和自我实现的渴望。
“从这一连串的现象中诞生的现代职业道德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在那之前,工作在所有文化里都被作为一种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 Hunnicutt说道。从古代希腊到农业社会,工作要么是被外包给别人的(通常外包给奴隶),要么就是一件应该尽快完成的事情,这样才能享受生活中的其它东西。
即使建立了新的工作道德规范,工作模式依然在不断变化,并不断受到挑战。在1800年至1900年之间,西方国家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从80小时减少到了60小时。从1900年到20世纪70年代,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进一步稳步减少,美国和英国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已将减少至40个小时。工会施加的压力、技术变革、开明的雇主和政府立法,所有这些都逐渐对工作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冲击。
有时,经济冲击会加速了这一过程。在1974年的英国,面临国际石油危机和矿工罢工导致的长期能源短缺,Edward Heath的保守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每周工作3天的工作制。这种工作制持续了两个月时间,在这两个月时间里,人们的非工作生活扩大了。在这段时间里,高尔夫球场的生意越来越繁忙,而渔具店的销售额也出现了大幅增长。收听深夜BBC电台节目的听众增加了两倍。一些男人也开始做更多的家务活:科尔切斯特晚报采访了一名年轻的已婚印刷工人,他已经承包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活。就连《每日邮报》的报道内容也放松了,一位专栏作家建议家长们在孩子们在学校的五天时间里尝试过更多的性生活。
英国的这个政策并没有持续下去。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重新定义工作或完全逃避工作的想法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变得非常常见:从企业户外拓展到反主流文化再到学术界,一种新的学科开始建立:休闲学,对体育和旅游等娱乐活动的研究。
1979年,当时著名的美国记者Bernard Lefkowitz出版了一本名为《Breaktime: Living Without Work in a Nine to Five World》的书,这本书是基于对100位放弃工作的人的采访内容创作出来的。他采访过一名之前主要从事修补船屋的建筑师;也采访过之前担任过记者的人,现在自己做番茄罐头,没事会听很多歌剧;他还采访过一名曾做过清洁工的人,他现在非常享受日光浴,并在阳光甲板上俯瞰太平洋。许多被采访者都生活在加州,尽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困惑和怀疑,但他们在放弃工作后依然感受到了“生活的完整性”和“体验开放性”这种全新的感受。
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有可能相信,工作至上的时代可能会在相对更舒适的西方国家走向终结。节省劳动力的计算机技术首次得到广泛应用。频繁的罢工让传统的工作制度被不断打断并受到挑战。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工资已经足够高了,这使得缩短工作时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到了这时,工作的意识形态被再次强加进来。在80年代,积极支持企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政府加强了雇主的权力,并开始利用削减福利和道德修辞的方法为没有工作的人创造了一个更加严酷的环境。David Graeber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名人类学家,他认为这些政策是出于对社会控制的渴望才制定的。Braeber表示,在经历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动荡之后,保守派害怕未来每个人都变成嬉皮士并放弃工作。他们在想:“如果真的这样,社会秩序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阴谋论,但是已经研究了西方工作潮起潮落近50年的Hunnicutt表示Graeber说的有道理:“我确实认为掌权者有一种对自由的恐惧,他们担心人们可能会找到一种比为资本主义创造利润更好的东西。”
在90年代和2000年代,支持工作的反革命运动被中左翼政治家们进一步巩固。在英国,在托尼·布莱尔政府的领导下,工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达到了顶峰。失业率达到几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工作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大多数人的工资都在上涨。新工党制定的最低工资和工作税收减免补贴政策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贫困率稳步下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是该国最著名的工作狂之一,他似乎找到了一种将工作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的公式。
左翼的很大一部分人士总是围绕工作来组织自己。工会积极分子为了保持这样的政策而努力,他们反对裁员,有时通过获得加班协议来延长工作时间。在这个严肃而有目的的大环境下,反工作的传统可能会显得有些颓废。在1993年创办的《Idler》杂志是英国为数不多的呼吁反工作的阵地。这个杂志虽然发行量不大,但却受到了狂热的崇拜。在杂志优雅复古的页面里,通常是一些相当时髦的人写的关于懒惰的快乐的文章。到了21世纪初,工作文化似乎变得不可避免。
(四)
现在的工作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在美国,近期的一些观点犀利的书籍已经开始挑战现代雇主的独裁权力和假设,同时也挑战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更加努力的工作是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书籍包括哲学家Elizabeth Anderson著作的《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和历史学家James Livingston著作的《No More Work: Why Full Employment Is a Bad Idea》。
在英国,即使是专业乐观的商业期刊也开始记录工作危机的程度范围。在经济学专栏作家 Ryan Avent在2016年出版的《 The Wealth of Humans: Work and its Absence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他预测,在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社会体系出现之前,自动化将会引发一段痛苦的政治变革时期。
关于后工作时代的想法也开始在政党政治中流传。去年4月,绿党提议将周末时间从现在的两天延长至3天。2016年,英国影子内阁大臣John McDonnell表示,工党正在“开发”一个在英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UBI)提案。去年9月,工党领袖Jeremy Corbyn在他的政党会议上说:“自动化可以成为工作和休闲之间的新解决方案的大门——一个扩展创造力和文化的跳板。”
“这感觉就像一个分水岭。” Will Stronge说,他是英国智库Autonomy的负责人,这个智库是去年成立的,旨在研究工作危机并找到走出危机的方法。“我们一直在和工党联系,我们很快就会与绿党会面。”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在政治上属于左翼分子,是在Corbyn的领导下成长起来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其中一员。Stronge承认,他们还没有与右翼人士交谈,因为没有右翼人士愿意与他们联系。
然而,后工作主义可能会吸引保守派。一些后工作主义者认为,工作不应该被废除,而是应该重新分配,让每一个成年人的工作时间都大致相同,同时不会让人感到精疲力尽。“我们可以对右翼人士说:你们认为工作对人有好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每个人都应该享受这个好处。更少的工作应该对那些重视家庭的保守派也会有吸引力。” 后工作主义者James Smith这样说道,他白天的工作是在伦敦大学的皇家霍罗威学院教授18世纪的英国文学课。
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各自孤立的强烈的工作文化之外,减少工作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主流观念。2000年,在法国,Lionel Jospin的左翼联盟政府为所有员工引进了每周工作35小时的工作制,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降低失业率、促进性别平等,他们当时的口号是“更少地工作、更多地生活。”这种每周工作35小时的工作制并不是绝对的,一些加班是允许的,但是自实施以来已经被逐渐削弱,但是有些雇主选择保留每周工作35小时的工作制。德国最大的工会IG Metall代表的是电力和金属工人的利益,工会正在发起一场让需要照顾孩子或其他亲属的工人有权利选择每周工作28小时的工作制的活动。
即便是在英国和美国,90年代和2000年代流行的“放慢生活节奏”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表明,繁重的工作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活。但这些都是针对个人的解决方案,而且通常是针对富人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针对整个社会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旨在给自由市场经济带来最小的破坏,而自由市场经济仍然相对是受欢迎且能发挥作用的。我们不再是那个世界了。
(五)
然而,当你遇到后工作主义者时,摆脱工作的负担和满足感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探险家们被忽视了几十年,就像Keynes和其他那些挑战工作规则的思想家一样,他们在自信和怀疑之间不断交替着。
“我热爱我的工作,我在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我时时刻刻都在做管理、做标记或写东西等方面的工作。我在做一份相当于两份工作量的工作。”西伦敦大学传媒与传播学教授Helen Hester告诉我。有一次我在一家咖啡厅采访她,咖啡厅里的其它顾客都在用电脑工作(一个无处不在的被工作殖民了的现代休闲案例),他故意疲倦地说道:“后工作其实就是有很多工作。”
然而,后工作主义者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被工作吞噬了,同时他们感到白领工作越来越不稳定,这促使他们要求一个不同的世界。和很多后工作主义者一样,Stronge多年来签的一直都是短期的低薪劳动合同。“我做过早餐厨师。我曾经也做过Domino的送货司机,我在教书的时候还曾在一家印度餐馆工作过。我的学生们有时会过来这家餐厅吃饭,看着我做饭,然后说:“Hi,Will,原来你还在这里工作。”
像商业领袖和主流政治家这样的工作文化的捍卫者会习惯性地质疑,被抑制的现代劳动者是否有能力享受甚至生存下来,这只是一种后工作主义者所设想的一种自由远景。1989年,芝加哥大学的两名心理学家Judith LeFevre和Mihaly Csikszentmihalyi进行了一项著名的实验,他们的试验结果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招募了78名在当地公司从事手工、文书和管理工作的人,并给他们提供电子寻呼机。在一周的时间里,研究人员会频繁但随机地联系这些员工,不管这些员工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里,并要求他们填写一份关于他们正在做什么和他们感觉如何的调查问卷。
实验发现,这些人在工作中比在闲暇时有更多积极的情感。在工作中,他们经常处于一个被心理学家称为“流动”的状态——充分利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来享受这个时刻,同时学习新技能并增强自尊意识。远离工作之后,这种“流动”状态就很少出现了。不工作的时候,员工们主要选择看电视、试图睡觉等,尽管他们不喜欢做这些事情。心理学家由此得出结论,美国工人在非结构化的空闲时间里无法组织他们的精神能量。
对于后工作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发现只是工作文化已经变得不健康的一个标志。我们做其他事情的能力就像萎缩了的肌肉一样,通过锻炼是可以恢复的。“休闲是一种能力。” Frayne说道。
Graeber认为,在一个不那么劳动密集型的社会,我们做工作以外的事情的能力可能会重新恢复并建立起来的。“如果你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人们是能想出一些要做的事情的。我曾经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村庄里生活过。在那里,有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交能力。人们会在咖啡馆里闲逛、闲聊、做风流韵事、使用魔法,就像是一部非常复杂的戏剧,只有当你有足够的时间时才会发展出这样的能力。他们当然不会感到无聊。”Graeber说道。
Graeber认为,在西方国家,工作的消失会产生一种更丰富的文化。“战后的岁月里,人们更少地工作,靠救济金生活更容易,当时人们创作了垮掉的一代诗歌、先锋剧院、50分钟的鼓独奏,以及所有英国伟大流行音乐,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才能创作和消费的艺术形式。”Graeber说道。
鼓独奏的回归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进步观念。但是,后工作时代的可能性,就像关于未来的所有设想一样,在太具体和太幻想之间走了一条艰难的路。Stronge为后工作时代的居民每天要做的事提供了一个建议,其中包括国家的干预程度:你从政府那里拿到全民基本收入,然后你会拿到当地议会的一份表格告诉你在所在社区要做的事情的情况:比如五人制足球比赛或其它一些社群活动。” 他提出的其他方案可能会让那些梦想能够不间断休闲的人感到失望。“我不认为有报酬的工作会完全消失。到时,工作可能不是由别人来指挥和控制的,而是你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你可以吃一顿很长时间的午餐,然后把工作分散到一天中的其它时间。” Stronge说道。
今天的城镇和城市中心基本都是根据工作和消费形成的,它们是工作的同谋,这也是后工作时代的世界如此难以想象的原因之一。将办公大楼和其他办公场所改造满足其他目的的场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那些后工作主义者才刚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种常见的提议是建造一种新型的公共建筑,这种建筑通常被认为是装备精良的图书馆、休闲中心和艺术家工作室的组合。“后工作时代的公共建筑可以有社会和保健空间,有用于编程的设备,有用于制作视频和音乐的设备等,它将不仅仅是一个社区中心,否则是会非常令人沮丧的。”Stronge说道。
这种由国家支持的、自由的、有生产力的公民的愿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Ivan Illich,这是一位快被遗忘的奥地利社会批评家,他在70年代曾是左翼的权威。在他在1973年写的《 Tools for Conviviality》这本书中,Illich抨击了工业机械创造的农奴制,并要求:“给人们提供工具以保证他们有权高效独立地开展工作,这些工具包括动力钻机和机械化手推车。”Illich希望公众能够重新发现他所看到的中世纪工匠的自由,同时也能接受最新的技术。
在今天的后工作运动中,有一种很强的工匠倾向。正如Hester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不再有工作,而是自己手工做自己的衣服。这完全是一种排它性的愿景:要做这些事情,你需要身强力壮才行。” 她还发现了一个更深层的保守冲动:“这就好像有些人在说:既然我们向工作发起挑战,其他的事情就必须保持不变。”
Hester希望后工作主义运动能更彻底地思考核心家庭。她认为,核心家庭是由工作塑造的,后工作时代的社会将会重绘它。有偿工作的消失最终可能带来女权主义最古老的目标之一:做家务和养育孩子的地位已经不再低了。她建议,随着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拥有可能更少的钱,私人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公共,不同的家庭会共享厨房、家用电器和其它设施。之前有过这样的例子,比如20世纪早期的‘红色维也纳’,当时社会民主主义城市政府建造了有公共洗衣房、公共工作坊和豪华的共享生活空间的住宅区。后工作时代是关于未来的,但它也充满了过去丧失的可能性。
(六)
既然如今的工作已经无处不在,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今天的“后工作主义者”能不能在他所有的前辈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呢?在英国,关于后工作主义运动的最尖锐的外部评论可能来自Frederick Harry Pitts,他是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一名讲师。Pitts曾经也是一名后工作主义者。他是一位年轻的左翼人士,进入学术界之前他曾在呼叫中心工作:他知道许多现代工作是多么的可怕。但是Pitts对后工作主义者想象的生活(创造性、协作性的高尚生活)与他们正在过的生活有多相似表示怀疑。“难怪记者、学者、艺术家和创意人士对后工作主义思维的理解如此到位,因为对于这些群体来说,传统工作的替代品几乎不需要适应。”
Pitts还认为,后工作主义的乐观愿景可能是一种避免世界上权力问题的方式。“后工作时代的社会旨在解决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它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所在。” Pitts说道。他说,厌倦了让工作变得更好这种无休止的工作,一些社会主义者已经被后工作时代所吸引,他们希望通过彻底摆脱工作来结束被剥削的命运。他说,这既是失败主义者的想法,也是幼稚的想法:“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永远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然而,Pitts对后工作主义者提出的有些建议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更公平地分配工作时间。“关于工作必须要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想要做出正确的改变。“其他批评后工作主义的的人也不像他们第一次听到后工作主义时那么不屑一顾。尽管Nick Boles是保守党里最亲商的一名议员,但Boles在他的书中承认,未来的社会可能会重新定义工作,将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同样视为是一种工作,并最终开始以恰当的方式评估这些工作的贡献。后工作主义将女权主义思想传播到了全新的地方。
Hunnicutt,这位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对后工作主义的想法更加抗拒,至少现在是如此。2014年,当他为网站Politico写一篇呼吁缩短工作时间的文章时,他对自己的文章所引发的强烈反响感到震惊。“那是一段艰难的经历,有人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认为我是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者和魔鬼崇拜者。” Hunnicutt说道。“工作的角色之前曾经发生过深刻的变化,它会再次发生变化,可能已经在变化的过程中了。千禧一代知道,能满足你所有需求的理想工作已经不在了。”
在Bristol会见完Pitts之后,我去了一个由Autonomy组织的后工作主义活动。那是一个寒冷入股的周一晚上,但自由主义的Bristol喜欢社会实验,这个位于市中心的活动房间几乎满了,里面有学生,有30多岁的专业人士,甚至还有一个中年农民。他们仔细地听了两个小时,Frayne和其他两名成员列出了工作中存在的压迫现象,然后又模糊地描述了什么可以来取代工作。当观众最终提问的时候,他们都接受了后工作主义者的基本前提。对一个以不同方式对待工作的社会的兴趣当然是存在的。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兴趣没有达到压倒性的程度:当晚参加活动的总人数还不到70人。
然而,正如Frayne指出的那样: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工作社会中了,但它是一个糟糕的后工作社会。办公室职员经常通过上网来打断自己的长时间工作。零工经济工作者,他们的劳动对他们的身份意识没有帮助。
去年10月,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研究表明,英国的失业人数是领取救济金人数的三倍,这要么归功于那些在经济上不活跃的人(他们不再寻找工作),要么归功于那些领取丧失工作能力福利津贴的人。当Frayne不谈论和写有关后工作话题的文章时,或者不再从事临时的学术工作时,他有时会通过为威尔士政府收集社会数据来谋生。“失业的种类有很多,但却没有社会政策来美化它。”
如今,要想创造一个更加良性的后工作世界,这要比70年代时更加困难。在今天的低工资经济中,建议人们做更少的工作来获取更少的工资是非常困难的。就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一样,工作变得越糟糕,想象逃离它就越难。
但对于那些认为工作将按照今天这样继续下去的人来说,历史上有一个警告。1979年5月1日,现代工作文化最伟大的拥护者之一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当选首相前做了最后的竞选演讲。她在演讲中反思了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本质。她说:一个阶段的异端派总是成为下一个阶段的正统派。工作的终结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它真正发生的那一刻。
原文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jan/19/post-work-the-radical-idea-of-a-world-without-jobs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