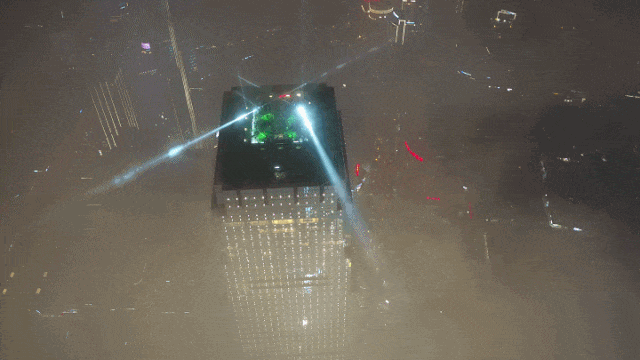在寒冬里跨年的地下夜店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未来品牌Daily”(ID:onebillionbrands),作者:独自跨年的,36氪经授权发布。
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商业夜店
说到夜店,大多数人会想到昂贵的酒水、绚丽的灯光、强烈而单一的音乐。你和一帮朋友在卡座上坐下,点一套88888黑桃A神龙套装,小姐姐们结队出现,拿着闪光灯牌围着你们绕圈圈,拉两炮礼花,纸花飞舞。于是全场都知道你是个人物,巨有面子。
这种商业夜店以外,其实还存在一种入场费仅0至100元,酒水一杯几十块的地下夜店(一些人更愿意称之为「俱乐部」)。地下夜店许多真的在地下负一层,远离商业夜店扎堆的工体西路。它们没有昂贵的灯光设备和百大DJ、甚至连座位都很难见到,主打的是风格多变、更具艺术性的音乐。
地下夜店是个存在已久的小众生意。早在2000年,就出现了很多现在已经消失的夜店:丝绒,Club Vogue, Orange,Green。很多迪友和业内人士甚至认为,地下夜店是九十年代迪斯科舞厅的延续,不算二十一世纪的新生事物。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并蹦上了「地下迪」。相对的,全国各地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地下俱乐部:北京上海自不用说,一些省会城市的地下夜店也形成了一定规模,并开始专业化。
我们和夜店老板、活动策划、DJ(「唱片骑士」)、蹦迪爱好者聊了聊,希望能管窥这正愈加热闹年轻人去处。
我是谁?我在哪儿?
商业迪常客壹跟我们讲述了他第一次去地下夜店「DADA」时的手足无措。
导航到达后,要不是门口聚集的吞云吐雾的青年们,壹一开始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眼前只有一幢破旧的矮楼,仔细一看才看到矮楼左下角「小得好笑」的DADA标识,跟工体西路上巨大又光鲜的夜店外设形成强烈反差。
「DADA」门外
因为当天是周末,DADA内部不足800平方米的面积显得逼仄。一个中央吧台把空间割裂成两部分:一边是座位区,一边舞池。「座位很少,就三四桌,而且还是很家常的那种座儿。」
他对DADA第一印象是简陋。店内四周都是刷黑的墙,舞台区不到10平方米,甚至连厕所都没有。因为座位早没了,他只能站着。DADA里没有商业夜店卡座上鞍前马后的专属服务员,要点酒的话要撵过拥挤的人潮,嘶吼着嗓子向酒保喊单。酒单上没有昂贵的洋酒,均价几十。
「DADA」的DJ台
但同时他又觉得DADA有那么一点儿酷。比起工体西路一麻溜儿穿大牌、潮牌爆款的人,来DADA的人显然更注重个性表达,「奇装异服」。
他意识到,这里与商业迪不同,不提供以男性为中心、易张扬财富的社交场景。
这种场景包括一眼就能识别顾客身份地位的区域划分(VIP包房,卡座区,散台区),桌子上用发光器材照亮的昂贵酒水,以及每份酒水套餐后接踵而至的美女礼炮。
资深迪友桔子告诉我们说,他几乎能一眼分辨那些第一次来地下夜店的人,他们不习惯没有卡座的环境,不知道手该放哪,有些人则会在点酒时问,「你们最贵的酒是什么?」
灯笼俱乐部主理人WengWeng也提到,「他们会在舞池里尖叫,围着圈跳舞,不顾周围其他人的感受。」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商业夜店里强势的区域划分让一些人无法找到存在感,而地下夜店相对包容,有更自由的空间,让他们得以释放压抑。
为了什么去地下夜店?
说出来你别不信,和我们聊过的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音乐。地下夜店的音乐形式要比商业夜店丰富得多。
商业夜店的音乐主要为EDM(电子舞曲)。但地下夜店的音乐会根据节拍、音乐元素、风格,细分到Techno(高科技舞曲),Drum and Bass(鼓打贝斯),Trance(「出神舞曲」),House(「浩室音乐」)等类别。
商业夜店里的EDM,不是用于聆听,而是用于制造氛围、有意图地操纵舞池里人们的行为。
「这是为什么商业迪厅的音乐有着固定的结构:由弱逐渐变强,然后进入到副歌部分,再然后突然一个空白,DJ开始喊麦『PUT YOUR FUCKIN' HANDS UP!』,气氛组开始尖叫。相应地,舞池里的人们一开始会蹦得比较柔和,然后疯狂开始甩头,最后配合漫天飞舞的厕纸和礼花、强闪光灯到达高潮。」桔子解释道。
地下夜店里,不少DJ也是音乐制作人。他们希望通过音乐来自我表达,而蹦迪的人也会去试图理解他们的音乐。
电子音乐派对组织「复古电工团」主理人SendersChen解释道,「在一个音乐风格约定俗成的规律和结构下,一些音乐人会通过加入鸟叫和风声来表达对自然的向往,另一些可能会加入城市的噪音和工业的打击声,来表达对都市生活的疑虑。」
舟舟作为聆听者,则这样表达她对地下夜店音乐的感受,「听宗教感浓一点的Techno,你会觉得你就是祭祀里边儿的一员,你还会感受到周围在刮风在下雨。听工业感浓一点的Techno,你会觉得自己在一个废旧的宫殿里,或者厂房里,对自己不断地发问。」
除了音乐,社交当然也是年轻人去地下夜店的原因之一。比起平日,在夜店里更容易遇到愿意开放地和陌生人聊天的帅哥美女。只是与商业夜店不同,地下夜店的社交并不会预设「消费很重要」。
此外,正如灯笼主理人WengWeng所说,社交不仅仅是关于「我和别人的关系」,还包括「我和自己的关系。」
「做音乐人十多年来,我很确定地观察到,大多数人哪怕是和认识的朋友一起去蹦迪,他们在舞池里常常都是以一种孤独的形式待着」SendersChen说。
一场酷爆了的地下派对是如何被策划出来的?
一场酷爆了的地下派对需要活动策划、场地方和DJ—— 当然了,还有那些能蹦迪到早上八点的「舞池永动机」们。
因为行业仍然小众,地下夜店的各参与方常会担任多重角色。SendersChen既是DJ,也是「复古电工团」的主理人,帮场地方策划复古风格的活动。WengWeng是夜店老板,但也做活动策划,偶尔也去其他夜店做串场DJ。
地下夜店的常规活动以参演DJ为核心,对外宣传着重音乐风格。
常规活动外,还有很多主题活动,比如北京著名地下夜店「招待所」在秦皇岛举办的海边音乐节。
再比如EXIT在长沙国际金融中心楼顶停机坪组织的Techno派对。
「歡迎光臨」厂牌在郑州市中心一个废弃10年的商场里,举办了一场太空主题派对。
活动中,策划方需要出主题方案、联系DJ、进行活动宣传;场地方提供场地和酒水;DJ负责制作和播放音乐。
场地是投入最重的一方。尽管是「地下」夜店,许多都处于主要商圈内或附近。比如,面积达1100平方米的灯笼在北京三里屯,每年租金不菲。地下夜店工作日一般不营业,即使营业,带来的收入也可忽略不计。与更主流且高消费的商业夜店相比,地下夜店无力承担诸如弹簧舞池、巨型LED屏幕等炫目的装置;它们一般装修简单,把有限的预算花在提升音响和灯光系统上。
地下夜店所承载的电子音乐行业还处于萌芽阶段。尽管近些年来涌现了不少DJ和厂牌,但他们目前还无法完全依靠音乐制作养活自己。在音乐制作外,绝大多数DJ和音乐制作人都在从事其他职业。
不同的场地会有不同的合作方式,一般来说是对票房进行分成。分成的比例,取决于DJ或者主办方的知名程度和票房历史,但一般场地方在二八到四六的区间内拿小头。除了票房分成,也有按酒水分成和支付固定出场费的情况。
各方的盈利,取决于最后能来多少人,以及这些人能消费多少酒水。地下夜店的核心消费人群会紧跟本地活动的讯息。所以主办方和场地方发发公众号文章,再动用下私域流量,就可以做到初步的推广。但圈内的一小拨人无法带动行业继续向前,从业者们还需要考虑怎样让圈外人也愿意尝试全新的文化体验。
两难的破圈?
业内有在做破圈的尝试。
SendersChen曾长期在学校门口分发传单、张贴海报,现在他更多是和同城公众号合作发布活动信息。
WengWeng认为,目前地下夜店在营销上的投入还不够,无办法让顾客清晰地明白地下夜店是什么,以及它和商业夜店的区别。
小众文化想要在大众市场得到认可,通俗化和刻奇化是无法避免的过程。同为地下文化的说唱音乐和摇滚音乐,在综艺节目的推广下,成功破圈,让地下说唱歌手和小众摇滚乐队得到了主流的关注。
但是,将地下夜店和其承载的地下电子音乐通俗化会面对两个问题。一方面,通俗化的地下电子音乐不就是商业夜店的电子舞曲音乐吗?地下音乐如何在通俗化后保持特色,和商业夜店的音乐有所区分,尚未有解。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业内的主要参与者们相当珍视目前地下文化的状态,并试图保护它。在WengWeng看来,相较于商业夜店的集体无意识狂欢,地下夜店宣扬的是独立思考的文化,并给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音乐选择。
「我会在商业和文化间寻找一个平衡,但是对于独立思考的尊重和选择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商业和文化之间出现了冲突,我肯定选择独立思考。」
SendersChen则认为任何想要投资地下夜店相关行业的资本都只能考虑长期投资,给「艺术」足够的成长时间。
除了通俗化方面的困难,地下夜店的产品也很难规模化。地下夜店提供的是一整套场景服务,电子音乐只是产品的一部分。灯光、音响、场景设计,甚至顾客的构成,都会影响产品的最终形态。WengWeng认为,只有实际体验才能带来对地下夜店比较准确的认知,营销主要还是得靠朋友间口口相传。
SendersChen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尝试牵手商业夜店,与云南德宏的一个主流夜店合办了场「复古派对」。「复古派对处于地下和主流之间。它是把多年以前的主流音乐拿到现在播放,用现在的舞池规矩和审美去重新编排制作」,SendersChen说,「当时效果特别好,所有人都很投入。当然也有坐在卡座上喝酒的。」
在上海,商业夜店众多的巨鹿路上,一家名为「44KW」的夜店也许提供了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44KW分为两个厅,一个厅提供传统的酒吧服务和现场音乐,另一个厅则是一个地下夜店。在酒吧里的顾客,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和尝试地下电子乐。我们去到44KW时,有接近100人排成长龙,远多于巨鹿路上的其他商业夜店。
「44KW」的传统酒吧厅
「44KW」的地下夜店
在寒冬里跨年
每年元旦前夜,北京的地下夜店门口都会排起长队,今年也不例外。「灯笼」作为北京最大的地下夜店,预售票早已售罄,只提供少量现场票,没票的人只能在灯笼提供的中巴车里避寒等待。
灯笼里装满了喜欢用蹦迪跨年的年轻人。三五成群的固然多,但也有同样多的人只带了自己,在时而神秘时而热烈的电音里,和上一年孤独地说再见。
这场派对在新年倒计时结束不久后被叫停。北京年底出现新冠病例,政策再次收紧。2020年,「灯笼」总营业天数不超过十天。截止发稿,灯笼依然处于闭店状态。
因公共卫生问题而闭店无可厚非,但随之而来的亏损也是确确实实。全国的夜店,商业或地下,都在2020年损失惨重。依靠往年的积累,北京的地下夜店坚挺地活了下来。但郑州、天津和昆明都传来了倒闭的消息。
选择继续经营下去的地下夜店,对未来都有比较乐观的判断,认为终将过去的疫情是目前的主要困难。灯笼决定在今年进行新的商业探索,希望把周内闲置的场地用于开展谈话节目、消费品市集、独幕话剧等文创活动。
也有人想要加盟灯笼,在广州、青岛开连锁俱乐部。但WengWeng拒绝了,「这不会成功。我觉得独立文化、地下文化跟主理人个人,TA的思想,以及TA的价值观有很大关系。它没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