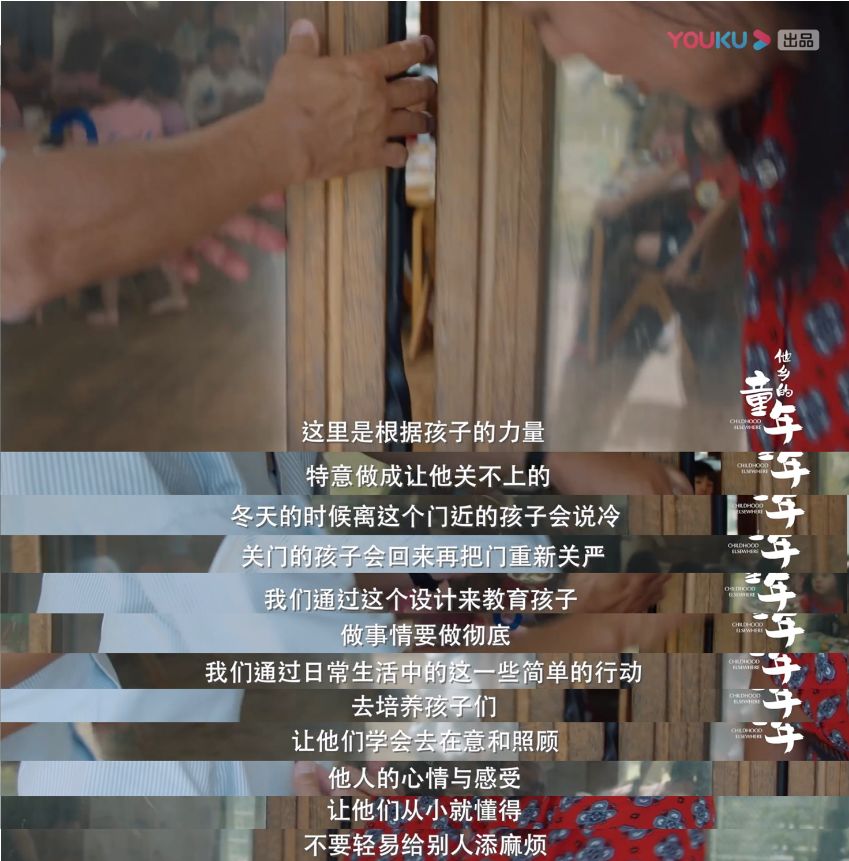战地记者跨越六国:中国式妈妈的一场世界教育“大冲撞”

我们身处在一个教育焦虑的时代。
这种焦虑感一方面来自外部环境的割裂——培训机构的广告每日轰炸在耳边,标准化考试、激烈的同代竞争,时刻提醒我们“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同样还是这个世界,“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的理念又不断从“精英妈妈”、教育KOL那里向外扩散,逃离应试教育、重新定义“学习”,看上去很美。
另一方面,“中国式家长”内心深处的自我困惑从未平息——一路奋斗才走到现在,我究竟要不要让孩子跟我走一样的路?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问我:妈妈,学习是为了什么?考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好像也很难给出一个好的回答。
对孩子来说,曾经的童年叫“夏天”、叫“抓虾”、叫“奔跑”、叫“无忧无虑”,如今的童年,被统一称为“起跑线”。
没有孩子的年轻人同样焦虑。他们焦虑的表现更加直接——不想生孩子。孩子一生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像一个沉重的负累让“这届年轻人”觉得窒息。
在没有孩子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孩子”。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身份只剩下“家长”。管教孩子,成为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矛盾和纠结中,中国家长开始寻找“解药”:母婴KOL、教育大V、育儿宝典、成长指南......
同样的困惑也落在了周轶君的身上。
以前,她是一位知名的国际战地记者,从混乱时局或战场上,快速发回掷地有声的报道。那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能在“现场”找到答案。
但面对孩子的到来,初为人母、比战地报道复杂一百倍的“教育”问题出现了。她尝试翻阅书籍、请教专家,寻找先进的教育经验。但伴随着理论输入的增多,困惑似乎有增无减:
芬兰的教育近乎被奉为“神话”,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的教育问题总被简单归结到“人口太多”,那么人口大国印度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日本和中国一样信奉“集体教育”,他们的“集体性”跟我们的定义是相同的吗?
带着这些困惑,周轶君踏上教育的寻访之路,选择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回到“现场”,从世界中找答案。
在这个过程中,截然不同的教育观念冲击、不同样本的碰撞、感动与感受、观察与思考,让这个典型“中国式妈妈”,沉淀下了更多关于教育本身的理解。
归国后,周轶君始终强调,这是她个人找寻答案的过程,并不试图说教、也不适用于所有的父母。和她曾经的记者身份一样,她只是尽可能把她看到的记录下来,把她的沟通方式和教育困惑暴露出来,她希望观者“看见”,而非全盘吸收。
在总结这次旅程的最大感受时,周轶君说:作为大人,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教育自己,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停止学习。教育,本质上就是我们与孩子之间,进行的一场平等对话。
旅程归来,我们和周轶君聊了聊这趟经历。和周轶君的出发点一样,我们也试图呈现更多的细节,而非贴出观点、作出结论。不论你是否为人父母、是否关注教育,希望都能从中有所思考。
毕竟,“教育”是一场终生的学习,我们每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
Q:从之前报道国际时事,到“停下来”投身拍摄一部教育纪录片,中间经历了什么?
A:从一名国际新闻记者到一位妈妈,不变的是思考问题的方式——从世界中找“答案”。
伴随年幼儿女的成长,我会遇到和所有妈妈一样的很多矛盾和困惑: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跟孩子沟通?如何在家庭场景中完成对孩子的教育? 等等。
举一个例子,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需要经常出差,每次离家前孩子都会哭的撕心裂肺,跟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啊、你为什么老是出差......如果是我的妈妈,可能很自然的会回一句:妈妈要上班呀,不上班谁来赚钱给你买玩具呀。
我总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对劲,但好像我也没有新的语言,来给孩子一个最好的回答。但当我走完这一圈,我发现,我要慢慢学会如何跟孩子讨论问题。
我开始对我的孩子说:这是妈妈的工作,妈妈觉得这份工作让我很快乐。我会拿出一张纸,让孩子列出“妈妈出差你喜欢的地方”和“你不喜欢的地方”。
比如我的孩子会写“不喜欢妈妈总不在家陪我”、“喜欢妈妈每次回来都会带来新的东西、好玩的故事”。我会跟孩子一起商量,规定好我每年出差多少次、每次最多多久、频率是怎样的,从中锻炼孩子的数学能力、对年月日的时间感知,我们达成这种契约,我也会遵守承诺。
从此以后,我的孩子再也没有因为我出差而哭过。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身份立刻变成一个“家长”。从没有任何一个培训或者考试,需要“家长”通过后才能上岗,我们似乎对此也习以为常——我们自己不就是这么长大的吗?父母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再教给孩子,一代又一代,不都是这样过来吗?
但是,我们上一代人的教育理念、我们习以为常的教育方式,真的是好的吗?
当我走过这么多国家,我慢慢体会到:当你知道了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你会变得不一样。而你的不一样,会决定孩子的一生。
Q:为什么选择“他乡的童年”,来作为重新理解教育的一个切口?
A:你我生活着的世界,就是孩子的“童年”,而童年是教育的“起点”。
我觉得童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一张白纸”的时候,我们对小孩子的态度、言语和教育方式,凝结了我们身处的整个社会的观念。
我们如何定义孩子的童年,决定了他们以后如何定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比如,我每次坐高铁都会听到大广播里呼号:“请不要在站台上奔跑”、“不要在站台上玩手机”,“列车停靠时间很短、请不要下车抽烟,车子很快就要开走了”等等一系列提醒。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社会对于成人管理的每一步,也都像是在管理小孩子一样。
难道一个成年人不应该知道自己不要乱跑、不要插队、不要乱丢垃圾这些基本规则吗?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最终都还是要归结到对童年的定义上。
铺天盖地的教养攻略和技术贴倒是也有,不断告诉家长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但似乎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教育孩子”这个底层命题。
所以我作为一个妈妈会有点疑惑:真的是这样吗?真的适合我和我的孩子吗?
比如,芬兰教育的先进性在国内几乎被神话。很多人会说芬兰的校内教育已经不分科了、学科之间全部打通。但当我到那里实地考察,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芬兰学校依然是有正常的分科,包括语文、数学、英文等等,另外会有一些融合性的线上教育课程。

做完这个片子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父母的眼界,决定了孩子的边界和未来。
我希望所有看这个片子的观者,能从我这个典型“中国妈妈”和世界各国教育者、家长以及孩子的沟通中,看到自己共通的问题,得到属于自己的启发和思考。
Q:片子里你走访了很多学校,也走进很多国外普通家庭,这些不同样本带给你的“冲撞”有哪些?
A:我们习惯于要学“有用”的东西、要考核“知识点”、“教”不好孩子是老师的责任...凡此种种,皆作“常识”。
亲历不同国家、学校、家庭,跟这么多教育者、老师、家长、孩子交流,我会发现: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长”,思维惯性不断受到挑战、观念被不断刷新。
比如在芬兰的一节“自然课”,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到森林里,我以为是要让孩子识记树木、学习对应的拉丁文名称,或者学习野外生存的技能这些有用的东西,不然去森林里“图什么”呢?

老师说不用啊,他只是让孩子们去感受自然而已。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去给树木取不同的名字,它可能叫“大海”、叫“天空”、叫“鱼”,叫任何名字。他还会让孩子去闻一些恶臭的东西,故意让他们去接触一些恶心的东西,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除了美的、香的、完整的,还有丑的、恶心的、破碎的。

他们会告诉我,作为老师,你只要、也只能把自己做到最好,你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我在学习。而对于学生来说,你们怎么看待学习这件事、你们是否像我一样学习,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这和我之前做新闻报道的感受完全一致:我们作为记者想要传递一个信息,其实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你改变不了所有人的观念、左右不了所有人的观点。你只要做到,我尽可能不主观、我看到的是这样、我传递给你,至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观众如何评判,不是我能决定的、也不需要我来背负。
Q:会不会思考这些完全不同的教育“样本”背后,底层共通的教育理念有哪些?
A:不要把孩子只是当成“孩子”,先把学生当成一个“人”。
每个国家的教育方式都各有不同,但走下来我会觉得,好的教育一定是先去定义“人”,一定不要把孩子简单视作一个稚嫩的小生命。
日本有句谚语:“孩子是父母的祖先”。父母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是孩子教育了你,是孩子让你快速“长大”,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教会你责任、沟通、爱以及很多很多东西。
我跟孩子制定的“妈妈出差规则”,是我去西安参加郝景芳的“童行学院”受到的启发。在童行学院,孩子们需要自己制定营规,需要根据自己的喜好、综合他们的习惯讨论出具体条例、然后达成一致。如果是大人来制定这个规则,孩子本能是反感的,但如果是孩子们自己讨论后制定的,大家会共同遵守并相互监督。
我去印度的一个学校参观,校长跟我说,你自己随便找两个孩子带你转转校园吧,这是他们的学校,不是我的。
然后两个大概6、7岁的女孩一边带我逛校园一边对我说,你知道吗,在印度,每6秒会有一个孩子饿死,we wanna stop it.(我们想制止这一切)
当时我就震惊了,也深受感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不要害怕跟孩子讨论一些关乎“价值”、“意义”的,看似“终极”的问题。
比如我会问我们家小朋友,你觉得你学习是为了什么?我女儿跟我说,是为了李老师...我当时哭笑不得。然后我会引导她:李老师会跟你一辈子吗?如果没有李老师,学习中还有哪些让你快乐的东西吗?诸如此类,展开跟孩子的对话。
总之,当你给孩子充分自主权的时候,他们会带给你很多惊喜和奇迹。孩子不是我的附属品、我的“勋章”,他们是和我们平等的、独立的一个“人”。
这些底层的教育原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亲子沟通中的无数个场景,而不局限某个具体问题。
Q:在这一系列片子中,每个国家的教育似乎都有一个标签,比如日本的“集体教育”、印度“爱的教育”、芬兰“快乐教育”、以色列“创新教育”等等,中国那一集似乎没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标签,回归我们本民族的教育,你最想探寻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A:传统与未来的关系。
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习汉字、接受传统教育,但与此同时,他们从很小就开始学英语、打游戏,接触的所有东西都是“世界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会思考:
我们的传统和未来是否会慢慢割裂?传统文化中,到底哪些需要让我们的孩子去继承、帮助他们面向未来?
我的女儿很小就同时学习英文和中文。慢慢我发现,其实孩子不应该太早学英文,英文表音、中文表意,英文学习相比于中文要容易多了。当孩子发现这一点后,会天然喜欢使用学起来简单的语言,中文基础反而打的不牢固。
又比如我们似乎对历史教育的重视不足。我们小时候背古诗,好像不太需要真正理解诗歌的意境,只需要背下来就好了、长大自然而言就能理解。旅程中我遇到一个插画师熊亮,他会把诗歌的意象画下来,帮孩子还原诗歌中的时间和空间。跟随郝景芳的童行学院去往西安,在一节关于兵马俑的历史课上,他们会回到现场、去讨论“what if”(如果..会怎样..)的问题,锻炼孩子的批判性思维。
所以,回到第一现场、还原历史、重新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传统,而不只是狭隘的把传统归结为“传统习俗”、甚至“伪国学”等等。
走完这一趟我忽然觉得,好的教育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指引”。
比如古代的“格物致知”,强调推究事物的原理,然后获得知识,知其然(what)、也要知其所以然(why)。这样我们学会的不止是知识,而是能让我们受益一生的能力。比如“因材施教”,强调个性化的教学。又比如近代的“德智体美”,我们的教育似乎不断窄化到了“智”这一个点上,品德教育、体育、美育都是匮乏的。
举两个细节,我在芬兰的时候发现,他们那里遍布大大小小的艺术馆、博物馆、美术馆,周末或下班去转一转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你带着孩子直接免费,他们没有专门的美育教育,他们觉得美是一种从小耳濡目染的熏陶。从小你的眼睛看到什么,长大就能创造什么。
另一个细节是,我们跟拍日本的幼稚园小朋友,一天下来我们的摄影大哥体力已经完全跟不上了,日本的小孩子还在快速的奔跑,体力非常好、说话声音也非常洪亮。他们每天给孩子安排的运动量是非常大的,会教孩子“呐喊”,他们把这些叫做“完全燃烧”,我非常喜欢这个词,它代表了旺盛的生命力和精气神。
审美、体能这些都是我们认为不那么重要的“学习”,但它会让每个人长大后的差别非常大,对精神面貌、气质、性格、品味、格局的改造,是非常不一样的。
Q:在国外这些普通老师和家长的眼中,“中国教育”和“中国家长”的面貌,分别是什么样子?
A:重视传统教育、教学效率高,但家长缺乏对孩子的鼓励和引导、对成功的定义窄化。
在我们走访的很多国家,老师会表现出对历史教育的担忧:他们发现孩子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不了解本民族的传统,他们认为中国在“传统教育”上做的很好。
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的教学效率很高,英国的一些公立学校会定期派老师到中国,学习数学课的大班教学模式——怎么样短时间内有效地把一群孩子的数学教好。
但是在国外教育者眼中,“中国家长”对孩子成功的定义似乎只有考试成绩,社会对于“失败”的容忍度很低,我们失败的成本很高、代价很大。
这带给我的反思是,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是不是过于窄化了。窄到就算学习一门乐器,也似乎只有“钢琴”和“小提琴”两种选择是最有用的,孩子想学打鼓、三角铁似乎都显得没用,哪怕他们非常感兴趣。
不论是考试考砸,还是创业失败,好像从此跟“looser”挂钩。在以色列,创业第四次失败相比于第三次失败,会获得更高的银行贷款,因为社会会认为你拥有了更多的经验、你很勇敢。
在我们的周围,你会看到太多看起来“成功”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们感到巨大的兴奋或者幸福,你从眼神中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心灵是干涸的,生命中只剩下“工作”和对于“成功”狭隘的定义。
小时候我们为了“分数”而学习,长大了我们为了“绩效”而工作,我们好像忘记了最简单的道理是:我们应该为了“生活”而学习,而学习应该贯穿我们的一生。
这衍生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似乎很轻易的会说出抹杀孩子“兴趣”、甚至抹杀“性格”的话。
比如,我们一起去芬兰的一个编导会很感慨,他说小时候很喜欢看侦探小说,他爸会跟他说,你不要整天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多看一些有用的书。从此他就再也没看过侦探小说,长大之后会觉得很可惜。
又比如我们会很轻易的取笑小孩子,“你唱歌真难听、你真的好胖、这个事情真的你不行的”。这些话说出来非常随意,但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如果孩子确实在某一方面有缺点,或者暂时没开窍,他们老师的做法是,在孩子喜欢的、擅长的领域里帮他补短板。比如一个孩子数学不好,但他喜欢车,老师就会陪他一起玩车,然后在小汽车里教他“数数”、教他“速度和计算”,老师告诉我,“那个东西会自然而然出来的。”
就我自己来说,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我女儿很喜欢画画,有一次我带着女儿一起画画,她画的超级开心,我记得好像画了一个冰淇淋走过公园之类的,但我半天下不去笔,好不容易下笔又涂涂改改,怎么也画不好。
最后开画室的那个人走过来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女儿不“害怕”画画,你“害怕”画画。
我就想到我小时候一直被取笑画画难看,从此不只没有再拿过画笔、也很难再特别放松的只是“画一幅画”而已了。事实上,艺术的表达从来无关“好与不好”,只是在于你“看见了什么”、你“自然而然的表达”。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喜欢的事情没有受到打击的话,他至少会作为一个爱好,至少不会为此而自卑或害怕,至少会在人生中的很多阶段,孩子心中会有一个信心和寄托。
Q:以“世界眼光”重新看待国内教培的狂热,会有新的认知吗?
A: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是家长共通的,不必妖魔化“中国家长”,新生代的选择正在不断改造“中国家长”。
我们好像总觉得“补课”是一种“中国现象”,但其实国外孩子也是要补习的,在竞争激烈的英国,20亿英镑的补习产业同样庞大。我们经常听到赞美芬兰“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的言论,但是放诸我们这么庞大人口的国家,真的现实吗?芬兰的整个社会都不鼓励竞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飞速发展中的国家,真的适合吗?
所以,对于“教育创新”的探索,可以再辩证和理性一点看待。
但是,国外家长的焦虑感之所以没有那么那么强,本质还是对成功的定义更宽广。

这让我想到我的一个朋友,在补习这件事情上她“抵抗”了很久,最后竟然是孩子的老师跟她说,你不给她补课,她比其他同学学的慢或者考的没其他同学好,就会让她没有信心。我这个朋友一下子就被戳到了,立刻给孩子报了学而思。
所以你看,这种焦虑是各种因素叠加的,是一时半会很难缓解的。这一方面可能是上面我们讨论的,整个大环境对于“成功” 的定义相对单一,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还在加速完善。
一些很好的变化是,国内也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芬兰的职业教育就一直做的很好,孩子就算考不上大学也可以去很好的职业学校,毕业后工作收入可能比大学毕业生还高,每一个专业、工种都会受到重视和尊重。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职业学校的专业,主要由行业工会制定,出口问题是可以保证的。
又比如,我回国后还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是,00后开始有了更多新的选择。有一个调查好像是说,00后最想从事的职业是当网红,我觉得很有意思。
新生代会主动告诉父母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他们认为人生不只是一个样子、一种模式的,独立意识的觉醒,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这种对父母的反向“教育”,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的改造“中国家长”,让他们也能从传统固有的思维中脱离出来,倾听自己儿女的想法、拥抱一个快速变化的新时代。
Q:很多人会说,教育的问题本质是经济问题、人口问题,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大、整体还处于高速发展期,客观上导致了教育资源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竞争激烈,这些看似“无解”的问题,能够从国外找到一些经验吗?
A:看似“无解”的问题如果不去解决,就永远没有答案。一个国家的教育问题是这样,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
确实,很多人一谈到中国的教育问题,就会说“我们人口多啊”、“我们也没办法”,所以我们有一集是去印度考察。
印度人口比我们还多,但他们在高精尖人才的培养上却非常出众、产生了非常多跨国企业的CEO;印度的校舍很破旧、教学设备很落后,但人们在线学习的意识却很超前。印度的贫困人口很多,很多家庭的生活在我们看来甚至是无望的,但他们的教育却能给带给孩子更多快乐和幸福感。印度是如何在混乱当中找到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值得研究。
还有一集是去日本,日本也被认为是跟我们很相似的国家,注重教育、注重集体性,但我很想知道,他们的“集体性”跟我们话语体系下的定义,是不是一回事?
在国外的很多国家,个体对于推动教育的创新非常努力。
比如印度学校的教育中有一个词叫“SOLE”(self-organized-learning environment),自我组织式学习,一些老师会自发把孩子们组织到一起学习,让他们通过互联网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话。
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男主角的原型,其实是印度的一位工程师,他很早就在印度的贫民窟中装平板电脑,让孩子接触互联网。后来他带着这个想法参加了TED TALK,并获得了三万英镑的大奖,于是又把这个计划扩大,发起了“云中学校”计划。
于是你在印度会看到非常“魔幻”的景象,穷到衣不蔽体光着屁股的孩子,坐在电脑前上网。
当地的老师会不停对我说,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孩子们不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他们真的会被整个时代淘汰。
在日本,他们的集体性指的是“照顾他人、重视他人的感受”,但我们理解的集体性好像更多是“规则、服从、整齐划一”。
我记得有一位校长在设计教室推拉门的时候,会故意设计一个“关不上”的自动推拉门,也就是最后一点缝隙必须要人来手动关上。冬天,坐在门边上的小朋友会非常冷,所以每个小朋友进出都必须随手把这个缝隙给合上。
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所以你看,每个国家、每个教育者都可以努力推动教育的变化,让我们的教育变得越来越好。我不太喜欢去把所有问题归结到“无解”的地步,因为它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就像我做这个片子的出发点一样,遇到问题,我就会立刻出发去寻找答案。
Q:您作为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高知妈妈,会思考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可能不一定代表更广泛的中国家庭吗?
A:到最后,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去找“答案”,我只是提供了一种寻找的方式。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的一位朋友在一个几百人的妈妈群里问,暑假她想带孩子去日本玩,有没有家长想组团一起?结果所有的家长都说,没时间啊,我们已经报好了XX补习班、XX兴趣班,结果听完,我这个朋友立刻就把旅行计划取消,送孩子去补习班了。
它背后反映的确实是家庭背景、教育观念的千差万别。
我必须要承认,面对没有那么多资源的家庭、家庭背景不足以支持孩子自由选择的父母,那种纠结和心疼:是的,孩子只有靠自己拼搏奋斗出来这一条路。
包括我之前去云南调研,我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什么叫“一块屏幕改变命运”,真真切切感受到什么叫做“不公平”。如果你生在一个教育资源没那么丰富的地方,你生来就要比别人更努力、甚至吃很多很多苦。
但我想说的是,不论怎样中国家长还是要思考一个问题:
孩子学习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孩子被逼到精神都要崩溃、在学生时代因为性格挤压而蒙上一生的阴影,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这样真的值得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再放松一点、深呼吸、喘口气,然后试着反思一下:
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冲刺的时候,那个终点真的是最好的吗?真的适合我的孩子的吗?即使有一天披荆斩棘到达终点了,然后呢?后面又是什么?孩子的人生难道到此就结束了吗?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过度“标准化”的社会,“班里的第一名就是优秀的,最后一名就是差生;数学好的就是聪明的,否则就是笨孩子。”
凭什么?我们的孩子凭什么要被这样分成三六九等、这样被定义?这是谁造成的?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刻板观念聚集起来、形成了这种无形但却强大的场域,把我们的孩子囚禁其中。
就我自己来说,我可能一开始的出发点主要还是解决自己的困惑,我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做一个片子就能够帮所有中国父母找到缓解焦虑的解药。
但我的这个片子也不会是终点,恰好相反它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会更加深入那些教育资源更不均衡的国家和地区,与那里的教育者进行连接、与当地的乡村教师、乡村校长对话。
比如,英国的寄宿制度,就非常适合乡村学校。很多很多人都在为解决教育不公平、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争取更多教育资源而努力,我也想要参与其中。
Q:片子全部做完之后,你最想给观者带来的是什么?
A:最开始做这个片子的出发点,只是去寻找教育我孩子的方法。但到最后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这趟寻访教育了我自己。
我希望每个人,不论你已经有了孩子、还是没有孩子,不论你关注教育还是不关注教育,当你有困惑的时候,都要自己去找“答案”。从你“出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不一样了,你的人生会因此变得开阔。
“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子。”作为大人,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教育自己,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停止学习。
受访者介绍
周轶君
《他乡的童年》总导演、知名战地记者。曾先后在新华社、凤凰卫视、 周末画报、彭博商业周刊任职,她的文字和摄影报道,涵盖中东及几乎所有世界热点地区,屡获国内国际奖项。
著有《中东死生门》、《走出中东》(又名《拜访革命》)等书,参与 《锵锵三人行》、《锵锵行天下》等访谈、旅行文化节目的拍摄。
关联阅读:「创业者」郝景芳 | 36氪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