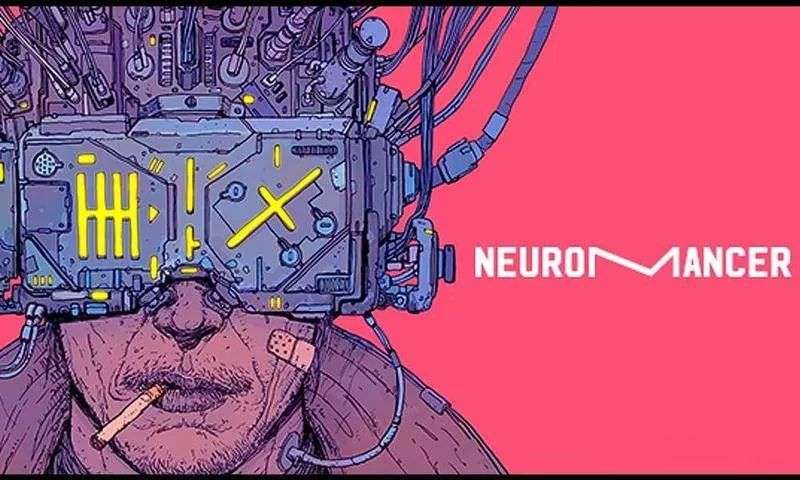赛博朋克2077:散装赛博,没有朋克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次元土豆”(ID:ciyuanpotato),作者:郭亨宇,36氪经授权发布。
先行者总是拥有对后来者批判的资格。
1982 年,一部后来被影迷们奉为赛博朋克电影“开山之作”的《银翼杀手》上映。当时,法国知名漫画杂志《咆哮金属》——这本堪称赛博朋克文化发源地的刊物,在电影上映后发表了一篇名为“菲利普·K·迪克的第二次死亡”的影评。
文章用尖酸刻薄的话语讥讽这部电影,认为菲利普·K·迪克在电影上映前意外去世是“幸运的”,否则,他将亲眼见证自己的小说、《银翼杀手》的改编原著《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在 70 毫米胶片大荧幕上被雷德利·斯科特这个可耻的广告业包工头谋杀”。
《咆哮金属》不买账。这本杂志认为,把菲利普·K·迪克精心打造的故事放置在一个充满迷雾,阴雨连绵的湿冷夜晚和错综复杂的城市里,是一件愚蠢的事,是矫揉造作地呈现元素而放弃了故事。
没有料想到是,曾经这些被瞧不上的东西,在 38 年后的今天统统成了“赛博朋克”的经典要素。风水轮流转,现在,评价的资格转交给了《银翼杀手》。
2020 年 12 月 10 日,由波兰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CDPR)开发的游戏《赛博朋克 2077》正式发售。
这款游戏很快占据各大游戏媒体的头版,IGN 认为它呈现出了“绮丽耀眼的城市景观”,PCGamer 对游戏品质给出了“令人惊喜”和“难以置信”的评价,在 Metacritic 上,有 15 家游戏媒体给了这款游戏满分。
一天后,《赛博朋克 2077》就为它的开发公司挣回了本钱。
《赛博朋克2077》中打造的城市景观
尽管这款游戏在首发日后因为大量 bug 和糟糕的优化问题饱受玩家诟病,游戏内的基础机制也充满瑕疵。
在 8 年的开发周期和接连跳票之后,首发游戏的成品仅能达到及格线标准。但这些技术问题最终总能修复,如果仅从娱乐产品的角度出发,《赛博朋克 2077》早晚都将成为当下游戏工业所能做到的最精美的玩具之一。
而假使我们抛开技术上的总总缺陷,就会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一款以“赛博朋克”为名的游戏,创造出了迄今为止最具沉浸感的赛博朋克都市景观,却最终没能回到对这一名词所指向的母题的讨论。
如果《银翼杀手》尚且被批评为“菲利普·K·迪克的第二次死亡”,那么《赛博朋克 2077》则是为这一主题打造了一块华丽的墓碑。
当“高科技低生活”和“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在不断复制粘贴的过程中,脱离其原文本变成营销语句,赛博朋克的反叛意识和先锋性,也被光污染一般闪动的游戏画面和“成为夜之城传奇”的庸俗梦想所葬送。
后现代主义与自我追问
赛博朋克(Cyberpunk)一词,来源于对“cybernetics”(控制论)和“punk”(朋克)两个单词的组合。
前者是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于 1948 年提出的理论。他将其定义为一种“针对动物和机器系统中的控制与通信的研究”。
控制论的基本观点大致是,在大部分系统中,存在自洽的“信号回路”,系统中的行为会通过信号反馈给系统,而控制论的目的在于通过信号来控制系统中的行为和通信。
控制论最初应用于工科领域,直到 1950 年诺伯特·维纳写出了《人类对人类的使用(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
在这本书里,维纳将控制论推广到社会学领域,主张社会全面自动化和基于机械操作思维的社会治理方案。此后,控制论的定义逐渐宽泛,维纳的思想也蔓延到了艺术和哲学等多个领域。
至于朋克,则指 1970 年代兴起的音乐反叛运动,它通常与反乌托邦、反权威和解构有关。
控制论和朋克的组合,构成了赛博朋克基本的理念,即对一个可操控的严密系统的反抗。
当然,这种对赛博朋克的理解依然有些粗浅,不过我们可以从大部分赛博朋克主题作品中,找到这一类作品普遍的共同点:它们大都描绘了一个近未来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已经孕育出了成形且严密的社会秩序,还被某种思想隐秘地渗透——可能是全面义体化,可能是消费主义,也可能是虚无主义。
故事中通常有一个存在自毁倾向的主角,他们总是在执行某个(或多个)秘密任务,并时常陷入莫名其妙的自我揪斗,对“无所有”的反抗和对存在本源的自我追问之中。
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是经典的赛博朋克题材小说
从作品回到主题的溯源,可以发现赛博朋克的诞生或多或少与时代发展脱不开关系。
20 世纪前半段,人们普遍相信人类终将塑造美好未来。印象派艺术、存在主义哲学、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变化全面冲击着人们的生活,从艺术、哲学到科技的革新带来了现代主义的思潮。
对此,历史学家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描述称,当时现代主义已经演化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倡议,社会氛围弥漫着恢复“对当代世界的崇高秩序和目的感”的氛围中。
紧接着,一场波及全球的战争将幻想击碎。20 世纪的后半段,后现代主义从战后的废墟中诞生。
人们开始怀疑进步的必然性,美好未来的蓝图被反乌托邦的想象取代,战后的文化革命在全球上演。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亚文化青年群体主导的性解放、平权运动和嬉皮文化俨然成为对抗主流的新锐集团。
作为二战遗产的一部分,计算机行业开始发展。1959 年,仙童半导体公司开发出集成电路使个人电脑的设想成为可能,之后,首部基于集成电路的微型个人电脑原型机 IBM 5100 在 1973 年面世。
一年后,世界上第一个网际协议构想被提出,并促成此后 20 年里,互联网在全球铺开。
旧世界改头换面的时刻,新浪潮科幻小说运动同时发生了,诸如《神经漫游者》和《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的科幻文学作品在此间面世,奠定了赛博朋克议题的基础——来自互联网、人工智能和人类生活之间的联系与矛盾。
《银翼杀手》和《阿基拉》等作品为这一主题的视觉美学提供灵感;而押井守导演的两部《攻壳机动队》又进一步深入探索了赛博朋克背景下个体如何存在,和“存在”概念其本源的命题。
从新浪潮科幻小说运动开始算起,赛博朋克诞生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在这 50 年里,不断有创作者为这一母体做出新的解读和诠释,也让赛博朋克的概念最终变得立体饱满。
用21世纪的方式造“夜之城”
黑色的东京湾向远处伸展开去,海鸥从白色泡沫塑料组成的浮岛上飞过。港口后面是千叶城,生态建筑群落像一堆巨大的立方体,铺满了工厂的圆顶。
港口与城市之间的一些古老街道组成了一片狭窄的无名地带,这就是“夜之城”,而仁清街正在夜之城的中心。
《神经漫游者》中所描绘的城市,在当下的电子游戏中被创造出来。《赛博朋克 2077》故事的舞台就搭建在一座名为“夜之城”的城市——毫无疑问,这是对《神经漫游者》的致敬。
游走于夜之城,玩家很快会发现《赛博朋克 2077》对声色犬马的近未来城市的呈现,与它的前辈们如出一辙。
霓虹灯、浮空车、从九龙城寨照搬出的凌乱高楼和幽暗小巷,以及傲慢地耸立于城市中心,如一块雪白色橡皮的公司大厦,该有的都有了。
街头帮派成员和警员随时在身边爆发枪战,遍地都是酒吧,而所有路人都接受了程度不一的义体化,机械手臂、智能化眼球、身体上意义不明的金属插件印记,时刻提醒着玩家已经置身于赛博朋克的未来。
游戏内的义体改造元素比比皆是
不仅如此,CDPR 几乎把所有值得致敬的作品都塞进了《赛博朋克 2077》里:《攻壳机动队》中的脑部接口和光学迷彩成为玩家的武器;“所有这一切都将随时间消逝,如同泪水溶于雨中”被刻在夜之城边境的公墓上。
玩家能开到《阿基拉》中那辆让无数人梦想的金田正太郎的摩托车;《死亡搁浅》中的 BT 变成人体改造试验品之一;游戏中几乎每个技能图标都能在影史作品中找到原型。
大量的赛博朋克元素堆砌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感受。在初体验的惊喜过后,冗余的、依赖于视觉体验的元素重复出现开始令人感到审美疲劳,游戏角色中的造型几近模板复刻,不得不令人困惑:我们对赛博朋克的想象到此为止了吗?
事实上,《赛博朋克 2077》并不是第一款触碰赛博朋克题材的游戏。2017 年 Reikon Games 开发的《废墟》(Ruiner)就做出了以赛博朋克世界为背景的动作游戏,讲述了一个机械打手沦为黑客傀儡的悲情故事。
今年 4 月,Ion Lands 又在《Cloudpunk》中打造了一个 minecraft 风格的赛博朋克城市,营造出了置身于近未来世界的孤独感。如今看来,《赛博朋克 2077》所做的不过是用 3A 游戏的制作水准,将这两款游戏整合在一起。
《赛博朋克2077》中的游戏场景
总体而言,《赛博朋克 2077》除了将曾经同题材作品中的元素放在一起之外,并没有提供更丰富也更引人遐想的未来图景。这么说似乎对 CDPR 过于苛责,毕竟,当我们距离赛博朋克足够接近时,对它的想象很难不被现实所局限。
2020 年,美国国会针对苹果、谷歌、Facebook 和 Twitter 四家公司展开质询,赛博朋克题材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大公司垄断背景已经接近临近;
手机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每个人躯体的延申,人们用它阅读、通讯、订外卖、打卡上班。疫情期间推出的“健康码”更是数字化的管理系统奏效的体现,现在,手机不可或缺的程度已经开始影响人们从一座城市前往另一座城市——就像一块无法摘除的电子生物印记;
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和机械外骨骼技术逐渐成熟,往自己身上加装电子设备的“超人类主义者”开始出现,可实现义体化的未来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关于人肉搜索和个人信息泄露的新闻见诸报端,甚至一则谣言就能把一个人的生活完全扰乱,让我们意识到尽管黑客还无法通过网络给别人的大脑注入病毒,但侵入甚至毁掉另一个人并不难。
在现实的冲击下,赛博朋克的预言接连实现。它的先锋性已经得证,却没有创作者能就此给出关于未来的更多警示。
“无名之辈”还是“名垂青史”
2018 年《赛博朋克 2077》预告片发布时,《神经漫游者》的作者威廉·吉布森就直言:“看起来只是披了赛博朋克外皮的《侠盗猎车手》”。
他没有说错。从一开始,《赛博朋克 2077》就借游戏角色之口,抛出了一个看起来一点都不“赛博朋克”的主题基调:“你是选择当个无名之辈,还是名垂青史”?
围绕这个问题,《赛博朋克 2077》展开了它的故事:游戏中,玩家扮演了一位名为“V”的雇佣兵。V 在一次盗取人工智能芯片的任务中意外失败,并在逃离追捕的过程中将这枚芯片塞进了自己的脑子里。
机缘巧合下,芯片中的人格被激活。为了不让另一个人格吞噬自己的意识,V 必须一边抵抗头脑中的幽灵,一边寻求自救的方法。
而在自救的过程中,V 意识到人格的主人就是 50 年前用热核炸弹袭击了夜之城最大的企业荒坂公司的头号罪犯“强尼·银手”。强尼·银手就像一个传教士,时不时蹦出来为玩家灌输“大公司之恶”的念头:大公司夺走了农田,污染水源,垄断经济,是不折不扣的压迫者。
而他将带领人们挑起一场“人民反抗脱缰的社会体制的战争”。这些观点用近乎说教的方式强行塞给玩家,至于强尼·银手给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则是炸掉荒坂公司的大楼。
随着故事进行,V 将发现自己的想法与强尼·银手逐渐重合,甚至在某些时刻,两个人格不再能区分出彼此,最终,强尼·银手将引领 V 走上一段成为“夜之城传奇”的道路。
强尼·银手由基努·李维斯扮演
看起来眼熟吗?这就像把《搏击俱乐部》的剧本搬到了 2077 年——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双重人格和自我斗争的故事从来就不新鲜,关键在于讲述故事的方式。在文艺复兴时期,歌德用浮士德与魔鬼做交易的方式讲述它。
到了千禧年前夕,大卫·芬奇用“心灵之战”的方式讲述它。现在,CDPR 用杀死每一个游戏任务点中的所有敌人的方式讲述它。
在《赛博朋克 2077》的主线剧情中,对话内容基本可以跳过,每个任务的计划亦可忽略不计,你需要做的就是闯进每一个敌人的营地,把所有挡路的人杀死,然后找到前往下一个任务点的线索,开启下一轮的杀戮。
CDPR 完全弄错了重点,尽管战斗不可避免,但它从来都不是赛博朋克作品中最重要的事。
《攻壳机动队》为巷战后的巴特准备好了蓝调音乐和一听冰凉的啤酒;《神经漫游者》为凯斯留下一张纸条,此后他再也没见过莫莉;《银翼杀手》为罗伊·巴蒂下一场雨,成就了他雨中的深情独白,而《赛博朋克 2077》只能安排一场又一场重复的战斗和无聊的性爱。
那些属于赛博朋克的,游走于冰冷城市中莫名生起的思念,在永生面前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怀疑,以及就此引发的自我毁灭的冲动,统统消散了。
那些悲情的、微妙的、充满孤独感的情绪,被口号式的演讲、激烈的愤怒和血腥的战斗完全盖过。时刻在耳边响起的摇滚乐传递着躁动的情绪,《赛博朋克 2077》把问题简单化,既然树立了一个象征邪恶的稻草人,击倒这个稻草人便成为唯一的目标。
成为“无名之辈”还是“名垂青史”的选择贯穿游戏的始终,英雄梦的幻想成为《赛博朋克 2077》故事的内核,这又是一次 CDPR 对赛博朋克的误读。
且不提所谓“名垂青史”的前提在于承认一部“正史”的存在,并承认它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意义——这一理念与赛博朋克的反权威主题背道而驰。
更简单地考量在于,当人们生活在一个通过上传个体数据就能实现数字化永生的时代,“名垂青史”是否依旧如它在当下语境中一般重要?
《阿基拉》中的金田正太郎不是为“名垂青史”而驾驶摩托车冲进大爆炸中,《黑客帝国》中的尼奥也不是为了“名垂青史”吞下那个红色药丸。
所谓的“成为夜之城传奇”的执念,让《赛博朋克 2077》与赛博朋克的联系,仅仅停留于表面,停留于那个被无数人想象的光鲜亮丽的“夜之城”。
2017 年,同题材的《攻壳机动队》真人版将原作中意识上载的命题探索,浅化为打倒资本主义大魔头的剧情。
2018 年,同题材的《头号玩家》热映,曾经用于瓦解数字操控的网络世界成为逃避现实的温柔乡。
现在,轮到《赛博朋克 2077》:在故事的结尾,V 住进了豪华公寓,拥有了夜之城最知名的酒吧,他挑起的战争,以他与这座城市和解而宣告失败。
私人浮空车越过夜之城上空,也越过爆炸后的废墟,在那废墟之上,倒塌的荒坂公司大楼终将重新立起。
而赛博朋克的概念在一轮又一轮的商业滥用中,失去了对抗现实的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