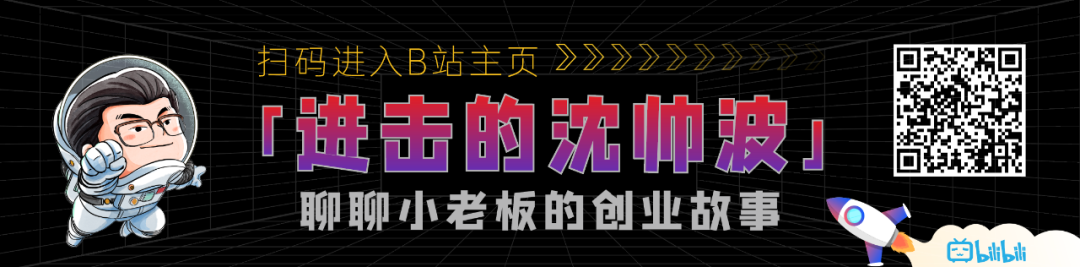
大年初二,我收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拜年微信,来自B站的一位粉丝。
他告诉我,他的丈母娘王丽华(化名)的菜摊上,单除夕夜前两天里,5车蔬菜,净赚6万元。
6万块,正好是袁春华所在城市的人均年收入,却在她的菜摊上2天内赚到了,全年统合下来,单靠卖菜这门生意,王丽华的年收入就已达到了百万。
过去少有人关注“卖菜”这样的小生意,超商近两年也频频被唱衰。但在这个被社区团购和生鲜超市围剿的寒冬,王丽华的菜摊却爆发着强大的生命力。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她的故事,撇开宏观洞察和经营的大道理,见微知著,我们从一个平凡个体的奋斗史中,来看看卖菜这门并不简单的小生意,以及菜场可能走向的未来。
(本文由我们原创的视频脚本根据文字特性修改而来。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鸭!各平台名字均为:@进击的沈帅波)
1996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了全国各地,国企改制的浪潮推动了一波创业潮。
王丽华就是身处浪潮的工人之一。她是浙江的一座县城的纺织厂女工,拿着一个月300多块钱的死工资,在时代洪流中接受飘摇的命运。
直到有一次,卖菜的老父亲让王丽华帮忙到镇上卖菜。这一卖,王丽华成了“下岗女工”。
她不是被开除的,而是主动辞职的。一方面,已为人母的她,嗅到了国企改制的 气息想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 ;另一方面,卖菜这个不起眼的小生意,收入却比在工厂打工赚得多,一天能赚七八十元。当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换算下来,只要卖5天菜,挣的比在工厂干一个月还要多。
它不是整齐陈列的超市,也没有遮风挡雨的大棚,而是一块约定俗成的空地,周边市民知道这里的菜贩集中,就会来这里购买。
在菜场,很多时候决定你收入好坏的,不是菜品是否优质,而是能否占据优质摊位。这在互联网思维里,被称为“得流量者得天下”。
为了占据一个好位置,王丽华要在凌晨3点半出发,否则来晚了,就连位置都没了。
有一次,在王丽华和父亲从村里往镇上赶的路上,三轮车出现故障,原来的好位置被其他菜贩占了,卖到最后不得不降价处理,收入比平时少一大截。
一个人抢的话,不能保证每天都那么早地到达,但一群人占位的话,总有人会先到的。王丽华由此联合其他摊贩,形成一个小团体。
为了能够保住好位置,王丽华和团队成员策划出设障、盯岗、值班、轮岗的方法。
他们用门板和砖头“圈地”,摆出“外人免入”的字牌,圈住的空位仅供团体菜贩使用。同时,小团体在附近租了一个房间,安排人守夜看管摊位。
尤其在卖菜“黄金期”的春节前后,摊位争抢最为激烈。团队会安排几户人家里最壮硕的兄弟,带上家里养的看门狗,直接睡在摊位上,让别人抢无可抢。
此外,王丽华还想到“一摊多用”。流动的菜贩都不是卖一整天的,于是“菜贩联盟”和“水产联盟”达成合作——同一块地皮上,在上午卖完海产的摊主,直接转交给下午卖蔬菜的摊主,充分开发了摊位资产。
当然,“菜贩联盟”并非长久之计,深究起来也不合法,占用公共空间必然引起争议。在抢位的过程中,“菜贩联盟”也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加之自然形成的流动摊位越来越多,缺乏管理,整个集市脏乱吵闹,严重扰民,经常被周边居民投诉。
没过多久,政府开始出资建立菜场,推动集市向规范的菜市场转移。
菜场建成后,如何说服菜贩向菜场内搬迁,成了难事儿。其中主要阻力来自于摊位费和经营范围的细分。
彼时,大多数菜农和王丽华一样,不是从批发渠道进货,而是卖自家种的菜。种多少,卖多少,做的是小批量、小成本的买卖,除了一辆三轮车,以及种菜过程中的种子、肥料,没有大额的固定支出。但一交摊位费,成本骤升,每月便有了固定支出,过损点大大提高,搞不好就是赔本买卖。
此外,菜场为了规范化管理,要求菜贩挑选、售卖一种类型的产品。若选择卖蔬菜,你就不能卖水产,若选择卖水产,你就不能卖鸡蛋。但很多菜贩在家中既种菜,又养鸡,还有人去捕鱼,最后都靠一辆小车拉向市场,支撑起全家的营生。
因此,在菜市场建成初期,小贩们不愿进驻,和城管展开了3年的斗智斗勇。凌晨三点半,商贩来抢位置,城管来围堵,当城管转头离去,菜贩又杀回来,重新占领阵地。
与城管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游击战”后,王丽华意识到,取缔流动摊位是迟早的事。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继续对抗下去,损人不利己。
最重要的是,越早进驻,越能获得优质摊位,这是新游戏规则下的洗牌。
在成为了第一批入驻菜场的菜贩后,王丽华开始帮助菜场人员,劝说打游击的流动菜贩,进驻菜场,以此换来菜场最好的位置。
在王丽华的协调和鼓动下,菜贩们相继放弃“游击战”,选择进驻菜场。随着入驻的菜贩增多,人们也纷纷前往菜场采购食材,菜场流量也就带起来了。
为了解决“自家种的菜不够,无法覆盖摊位成本”的问题,王丽华把菜场的流量运用到极致,开始向同村、隔壁村的菜农收菜。
这是从自产自销向渠道商转换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菜场经营过程中的折损,也推动着王丽华从C端生意,向B端生意进一步转型。
入菜场的第一年,菜摊生意出奇地好,也浮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讨价还价消磨精力”、“挑拣过程中带来的损耗”。
意识到这两个问题后,她将菜场的散客生意交给家里人打理,自己琢磨起B端的生意。
她瞄准了酒楼类的餐饮店,找老板、大厨谈供货。因价格好、品质优、种类齐全,以及维护客源的策略 (如采购对象是厨师的话,她会给一定的回扣) ,王丽华拿到大批量订单,也就有底气去30公里以外的蔬菜批发市场进货,那里的菜价更便宜,种类更多。
针对供给饭店后多出来的菜,除了在菜市场卖给散客,她还会以中间价,卖给之前小团体的那群人。
对于其他菜贩来说,因为量不够大,覆盖种类也不多,无法像王丽华一样去批发市场进货,否则还要再贴货运费。卖菜本是低毛利的生意,若做不出规模,很难负担此类成本。
至此,王丽华的卖菜生意从一辆三轮车来回奔波,变成辐射菜场内外的生意。
新批发的菜一般会按层级分销:先供饭店——再出货给同市场的菜贩子——余下的自己出摊卖给散户——被挑拣剩下的菜统一供给卖饲料的。“在我的摊位上,休想浪费一根菜叶子”,王丽华不无得意地感慨道。
生意模式搭建起来后,盘子做大了,但王丽华和家人并未做甩手掌柜。当人们准备进入梦乡时,王丽华和家人就开始了进菜、运输、配送的工作。
这些新鲜的蔬菜,会在第二天,成为饭店餐桌上的佳肴珍馐、菜场小摊贩的生计之本,之后被散客们带回家,支撑起每个家庭的平凡日常。
凭借这笔生意,王丽华在开启卖菜生涯的头几年内,快速攒下了百万资产,给家人带来了更好的生活。在奔向小康后,王丽华并未停下脚步,菜场的生意迎来了新的挑战。
起初,菜场的生意非常好,但由于管理不够规范,慢慢地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
一方面,一些小商贩搞假钞、假秤,水产经常灌水;另一方面,不愿搬进菜场的流动摊贩,截留了部分客源。因为没有摊位租赁成本,他们的菜能提供更低的价格。
2001年前后,国家开始推行“农改超”政策,推动农贸市场的社会供给职能,向超市转移。除了上面提到的问题,“瘦肉精”、“注水肉”等食品安全问题,也引起了管理部门的担忧。
一座座超市拔地而起,蚕食着菜场的生意。“内忧外患”之下,王丽华坐不住了,开始着手解决问题。
之于诚信经营,王丽华和早期的“菜贩联盟”成员一起,在自家摊位上设立一把公平秤、验钞机。消费者在菜场任一摊位买的菜,都可到这里核实重量,验钞。
该做法类似于“行业联盟”,通过成员间的互相监督,为消费者提供诚信保障。
另一方面,为减少流动摊贩的截留,她开始和“菜贩联盟”主动成为志愿者,帮助街道管理人员,拦截流动摊贩。
至此,王丽华实现了“卖菜的个体户→渠道供应商→‘规则维护者’和‘管理中间人’”的转变。主动承担管理职责,为她换来了更多摊位费上的减免,进一步压缩了经营成本。
在农改超政策推行过程中,也遇到阻力。老的农贸市场物业条件差,规模小,改造成本高——同等面积相比,“农改超”比新建生鲜超市成本要高出20%至30%。
因此,“农改超”政策转向“农加超”——农贸市场和超市共同发展的模式。在王丽华和菜贩们的共同努力下,菜场恢复了热闹。
在生意较好的那几年,菜场曾提出过涨租金。王丽华并未因享受自己参与管理获得的优势价格,而不管其他菜贩的生存,而是风险共担。
一方面,她联合整个菜场摊贩,把租金涨幅调整到最低;另一方面,说服不肯统一涨价的摊贩,在菜贩和菜场管理者的双重角色间,维系平衡。
疫情期间,买菜的人流大幅减少,饭店需求也被中断。王丽华组织起商贩,联名和物业谈免租,帮菜场摊贩们减少了损失,度过了“黑天鹅事件”。
而随着生鲜电商的发展,王丽华的菜场生意也受到影响,好在还有B端生意,但其他菜贩的生意成了水中飘萍。
少有个体的力量能够抵抗时代的洪流,但洪流过后也并非寸草不生。菜市场中虽然少了许多年轻人,但还有年迈的老人、下班后的中年人,习惯来买看得见、摸得着的新鲜菜,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依然人声鼎沸。
和“菜”打交道的25年里,王丽华赚得人生的一桶桶金,也从未懈怠过。一次次地发现问题,并勇敢地站出来,带头解决。或许有些处理方式,透露着些许粗糙和狠劲儿,但也是一种来自于泥土的敢打敢拼、敢爱敢恨。
许多人的致富故事,有聪明的部分,有时代的机遇,但更多平凡人的致富,靠的还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在一个领域深耕的决心。
如今,相比生鲜电商的冲击,王丽华更担心生意的传承。她早已到退休年龄,想把这半辈子积累的资源、渠道传给子女,而孩子们却不太愿意接手这“又脏又累”的行当。
王丽华菜摊的生命力,来自她的坚持和勇气,这样的精神,有时能够避开浪潮的冲击,但我们也很难忽视,执着坚守于市集小车和小店的菜贩们,也走向了人生的黄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进击波财经”(ID:jinbubo),作者:沈帅波,36氪经授权发布。












